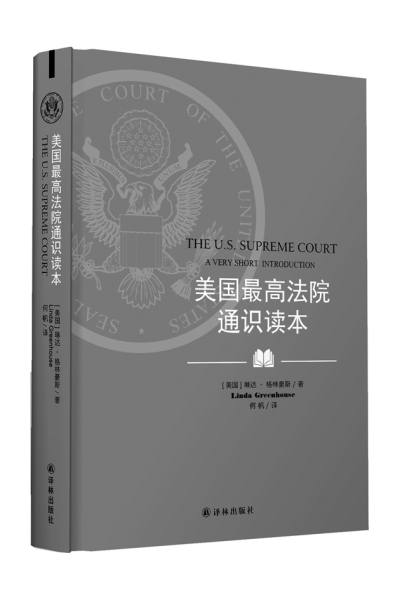《美國偶像》與九位大法官
“哪位朋友可以說出照片上所有大法官的姓名,我可以送他一本新書。”2013年1月26日,我在北京單向街書店參加一次以“律政劇、法律翻譯和司法文化”為主題的講座。開場時,為了活躍氣氛,我亮出美國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最新一張“全家福”,并向現(xiàn)場上百位聽眾發(fā)問。意外的是,居然有不少人舉手搶答。“羅伯茨、斯卡利亞、肯尼迪、托馬斯、金斯伯格、布雷耶、阿利托……嗯……索托馬約爾,還有卡根!”雖然答得有些磕磕巴巴,前排一位女孩還是準確說出了每位大法官的名字。
美國人要是目睹上述場景,肯定會覺得奇怪。因為根據(jù)2011年一項民意調(diào)查,55%的美國人連一位大法官的名字都說不出,32%的人不知道最高法院是干什么的,相反,65%的人卻可以完整說出選秀節(jié)目《美國偶像》三名評委的名字。這一結(jié)果,與全美中小學(xué)公民教育萎縮有很大關(guān)系,也令眾多有識之士憂心忡忡。
相比之下,中國民眾對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興趣,倒是在緩步升溫。從2008年的“特區(qū)禁槍案”到2013年的“同性戀婚姻案”,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的幾起重要案件,都成為中國媒體熱議的話題。一些經(jīng)典名案甚至著名判詞,也逐步為人所知。2012年初,國內(nèi)某位卷入“代筆之爭”的公眾人物欲提起名譽侵權(quán)之訴,無論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將1964年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判決作為論辯依據(jù)。某些網(wǎng)站肆意刪帖時,網(wǎng)民們也會引用威廉·布倫南大法官主筆的“沙利文案”判詞:“對公共事務(wù)的討論應(yīng)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并廣泛公開。”
法政圖書與文化傳播
從陌生到熟悉,是一個漸變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隨著國門打開,與美國最高法院及大法官有關(guān)的譯著,陸續(xù)進入國人視野。較著名的,有《美國最高法院內(nèi)幕》、《法官與總統(tǒng):一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等。進入上世紀90年代,經(jīng)過眾多法律學(xué)者的普及傳播,人們開始對美國的司法制度與經(jīng)典判例有了更加具體的認識。
然而,在最高法院文化傳播方面居功至偉的,卻不是法律人。由1996年的《歷史深處的憂慮》起步,林達女士的“近距離看美國”系列,從憲政和法律切入,通過介紹諸多案例,全面展示了美國的政治架構(gòu)、公民文化和司法議題。任東來先生和他的研究團隊則更進一步,在2004年推出《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一書,從最高法院的建立,一直講到2000年的“布什訴戈爾案”。這本書資料翔實、寫法生動,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遺憾的是,東來先生今年5月因病逝世,未能實現(xiàn)他深入推介憲政文化的宏愿,實在令人痛惜。
2007年之后,介紹聯(lián)邦最高法院及大法官的圖書種類更加豐富、視角更為多元。《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fēng)云》(以下簡稱《九人》)首度揭示了大法官內(nèi)部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黑衣人》從保守派視角,解讀了最高法院近些年的所作所為。《批評官員的尺度》和《吉迪恩的號角》則從經(jīng)典個案切入,贊頌了最高法院在維護言論自由、保障刑事人權(quán)上的努力。近十年來,卡多佐、霍姆斯、哈倫、布萊克、布萊克門、斯蒂文斯、倫奎斯特、斯卡利亞、奧康納、蘇特、布雷耶等知名大法官的著作或傳記,已陸續(xù)與中國讀者見面。“美國法律文庫”、“上海三聯(lián)法學(xué)文庫”和“社會思想譯叢”中,也包含許多與最高法院有關(guān)的杰出作品。
至少從目前情況來看,讀者們對這類圖書的興趣有增無減,還未進入“審美疲勞”狀態(tài)。這種興趣增長,既是受律政劇等法政文化廣泛傳播的影響,與近年國內(nèi)熱點事件多與司法個案相關(guān)也有很大關(guān)系。
是否存在“司法至上”
經(jīng)過各路學(xué)者的引介和傳播,國人對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認識大致如下:它與國會、總統(tǒng)并列,是構(gòu)成美國聯(lián)邦政府的三權(quán)之一。九位大法官由總統(tǒng)提名,參議院審議確認方可任命。大法官一經(jīng)任命,終身任職,任何機構(gòu)和個人不得隨意撤換。由于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爭得“司法審查權(quán)”這一重磅武器,大法官們可以解釋憲法,據(jù)此推翻國會立法或總統(tǒng)決策。兩百多年來,最高法院曾是保守堡壘,竭力抵制經(jīng)濟改革;也做過民權(quán)先鋒,主動推動社會發(fā)展。無論歲月如何變遷,最高法院始終是憲法的忠實守護者,深受廣大美國人民信賴。
上述認識,有制度上的客觀描述,也有流于簡單的美好想象。例如,身邊不少朋友就認為,大法官們有絕對的權(quán)威,是最后的決斷者,美國是“九個人統(tǒng)治的國度”。還有朋友喜歡引用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的名言:“在美國,幾乎所有政治問題遲早都要變成司法問題。”甚至提出,美國的一切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爭議,最終都可以拿到最高法院審理,由大法官說了算,并認為這種“司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境界。當然,也有人不這么看。有朋友讀完《九人》后,感嘆“美國大法官原來也要講政治,自由派支持民主黨,保守派支持共和黨,審判只是走過場”,甚至得出美國最高法院也是“政治化”法院的結(jié)論。
上述看法,有誤讀的成分,也有因?qū)Ξ斚卢F(xiàn)實不滿,而對異邦制度生出的美好想象。這種想象,可以理解為一種善意的期許。但是,如果司法改革者也按照想象中的圖景進行頂層設(shè)計,甚至考慮制度移植,結(jié)果卻可能適得其反。
2012年4月,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訪華時,我曾就美國是否的確存在“司法至上”這一問題向他求教。他回答,在美國,政府的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屬于政治分支,因為他們由人民選舉產(chǎn)生,目的是為公共事務(wù)做決策。而制憲者設(shè)置司法分支,不是為了讓它成為反映多數(shù)人意志的工具,因此,不能把法院看做政治機構(gòu)。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最高法院向來認為,政治問題應(yīng)該交給政治分支解決,法院不受理也不解決政治問題。例如,關(guān)于國會的選區(qū)劃分爭議,早期的最高法院就以這是政治問題為由拒絕介入。另外,最高法院既不掌握軍權(quán),也不把控財權(quán),是“最不危險的部門”,如果介入政治過深,判決執(zhí)行不力,反會降低司法權(quán)威。
布雷耶提出,最高法院應(yīng)該有所為、有所不為,與其他政府部門維持堅實有力、切實可行的工作關(guān)系,在決定是否受理案件或作出判決時,要充分考慮其他部門的憲法職能,包括他們的優(yōu)點、不足和運轉(zhuǎn)方式。這一思維,與我們對美式司法獨立和“司法萬能”的想象,其實有很大差異。國人常對“布什訴戈爾案”津津樂道,認為是大法官的關(guān)鍵一票決定了總統(tǒng)歸屬,但在多數(shù)大法官心目中,最高法院當時根本就不該蹚這灘政治渾水。13年來,從來沒有一位大法官引用過這個判例。
“司法至上”是一廂情愿的美好想象,“司法政治化”更是標簽式的判斷。談及最高法院大法官,許多人愛做這樣的分類,如斯卡利亞大法官是保守派,支持共和黨;布雷耶大法官是自由派,支持民主黨。有人甚至認為,與保守派因循守舊的原旨主義相比,自由派的務(wù)實解釋方法更接近憲法核心原則。初涉譯事時,我也好做這樣的派系劃分,因為簡單、明確,也易于理解,但隨著觀察逐步深入,漸漸覺得這樣分類太過絕對,容易把復(fù)雜問題簡單化,導(dǎo)致認識上的偏差。例如,斯卡利亞大法官在死刑、錯案糾正問題上立場保守,但他又是刑事被告人對質(zhì)權(quán)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被譽為“刑辯律師之友”,所以,很難把他的立場套到一個意識形態(tài)框框里去。另外,同樣是立場偏保守,斯卡利亞與羅伯茨、阿利托在很多問題上的觀點就不一致。的確,立場偏保守的大法官們近年推翻了不少先例,但立場偏自由的大法官早年推翻起先例來,也是毫不手軟。再說,到底什么是“憲法核心原則”呢?恐怕大家都認為自己堅持的才是憲法“正道”,而對方走了“邪路”。大法官們終身任職,就算跟之前任命自己的總統(tǒng)或政黨對著干,也沒人能拿他們怎么樣。人人皆有立場或偏好,如果把他們的個人偏好或選擇一律理解為依附于某些黨派,并不是公允評價。
在我看來,如果對某個機構(gòu)運行的歷史背景和制度土壤缺乏了解,任何贊美和貶低都是廉價的。因此,每當身邊朋友過度溢美或無故抨擊美國最高法院,我都會推薦他們閱讀幾本通識性讀物,如戴維·奧布賴恩的《風(fēng)暴眼》、亨利·亞伯拉罕的《司法的過程》,又或勞倫斯·鮑姆的《最高法院》,希望他們在深入了解之后,再做評價。
但是,也有人抱怨,這幾本書都是“大部頭”,如果不是對司法話題特別感興趣的專業(yè)人士,沒人能堅持讀下來。這就讓我犯愁了,因為在浩瀚書海里找一本能夠簡明、準確地介紹美國最高法院的小冊子,本來就有難度,如果還要求資訊夠新、門檻夠低,更是難上加難。如今,問題總算解決了,因為有了琳達·格林豪斯的牛津版《美國最高法院通識讀本》。
通識的力量
剛?cè)氪髮W(xué)時,一位老師曾告訴我,年輕時別急著猛啃經(jīng)典,先讀讀學(xué)術(shù)大家寫的小文章,看看別人如何化繁為簡,用平實的語言闡釋一門復(fù)雜學(xué)科或一套知識體系。后來依此行事,果然受益匪淺。牛津通識讀本系列,就是典型的“大家小書”。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這套系列叢書于1995年推出,每本對應(yīng)一個特定主題,介紹簡潔、精煉、準確。叢書皆由行內(nèi)公認的專家撰寫,涉及政治、法律、經(jīng)濟、文學(xué)、藝術(shù)、宗教、考古、生物、物理各領(lǐng)域,每本篇幅在120-150頁左右,“在不犧牲準確性的前提下,盡可能寫得簡單”。由于原書副標題為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所以被廣大讀者們親切地稱為“VSI叢書”。“最高法院通識讀本”就是2012年年初推出的“VSI叢書”之一。
按理說,像《最高法院通識讀本》這樣涉及諸多法史、判例知識的小冊子,出版社應(yīng)當約請著名法學(xué)教授、法官或資深律師執(zhí)筆,但最終選定的作者,卻是退休女記者琳達·格林豪斯。不過,只要看看格林豪斯的履歷和作品,人們不僅不敢質(zhì)疑她的資歷,反會認定她是撰寫本書的不二人選。
在美國,各大媒體在最高法院的“跑口”記者都是行業(yè)內(nèi)的佼佼者。這些人長期報道最高法院及其案件,多數(shù)人一干就是幾十年,不僅與大法官們交情深厚,更是最高法院事務(wù)專家。這些記者對最高法院的人事格局、內(nèi)部流程和案件內(nèi)幕如數(shù)家珍,不僅有大量膾炙人口的報道,還出版過不少以最高法院為主題的暢銷書。如《批評官員的尺度》作者安東尼·劉易斯,就曾是《紐約時報》記者,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大法官曾贊嘆他“比大法官還熟悉最高法院的情況”。《九人》作者杰弗里·圖賓是《紐約客》專欄作者。奧康納、斯卡利亞兩位大法官的最新傳記,也都由《今日美國》記者瓊·比斯丘皮克撰寫。
琳達·格林豪斯就是最高法院“跑口記者”之一。她1968年畢業(yè)于哈佛,1978年讀完耶魯法學(xué)院后進入《紐約時報》,在該報從事了30年最高法院事務(wù)報道,撰寫過2800多篇新聞稿,除1998年獲普利策獎外,還獲得過不少新聞獎項。在采訪過程中,格林豪斯與許多大法官結(jié)下了深厚友誼,2008年宣布提前退休時,九位在任大法官全部參加了她的榮休儀式。目前,格林豪斯仍在耶魯法學(xué)院執(zhí)教,并為《紐約時報》網(wǎng)絡(luò)版撰寫雙周專欄。
最能說明格林豪斯在美國司法圈地位的,是她為已故大法官哈里·布萊克門作傳的經(jīng)歷。布萊克門自幼勤寫日記,定期收存文獻,這個習(xí)慣一直保持到退休。1999年,布萊克門將私人文獻全部捐給國會圖書館。這些文獻多達50萬份,分裝在1585個紙箱里,里面既有他的日記、書信、課堂筆記、消費單據(jù),也有各類備忘錄、會議記錄、判決初稿,其種類之齊全、分類之細致、整理之嚴謹,令后人嘆為觀止。布萊克門去世后,親屬經(jīng)過慎重考慮,決定邀請格林豪斯優(yōu)先接觸這些文獻,為大法官寫一部傳記。
2004年,格林豪斯在國會圖書館埋頭工作了兩個月,隨后完成的《大法官是這樣煉成的》一書,因敘事簡潔、資料翔實而廣受好評,成為《紐約時報》2005年推薦的暢銷書之一。2011年,我曾有幸將該書譯為中文,兩年后,能再度受托翻譯格林豪斯女士的新作,是緣分,也是幸運。
化繁為簡的技藝
《今日美國》資深記者瓊·比斯丘皮克說過,從事最高法院報道30多年來,她經(jīng)受的最大挑戰(zhàn),不是如何挖掘某個大案內(nèi)幕,或者聯(lián)系采訪某位大法官,而是如何用平實、淺顯的語言,將復(fù)雜、專業(yè)的案件解釋給廣大讀者。闡釋案件尚且如此,介紹最高法院的歷史、制度和運轉(zhuǎn)更不例外。
接手翻譯本書之前,我也好奇格林豪斯如何能在一百多頁的篇幅之內(nèi),將與最高法院有關(guān)的種種知識介紹給廣大非專業(yè)讀者。畢竟,光是“馬伯里訴麥迪遜案”那樣繞不過去的偉大判例,案情介紹就可能占上好幾頁。如果作者把握失當,“讀本”很可能成為一本老調(diào)重彈的史料雜燴。
格林豪斯最終完成的作品令人驚喜,不僅詳略得當、敘述客觀,選材上也頗具新意。光是謀篇布局,就能看出本書的“通識”特征,幾乎每一章都回應(yīng)了普通讀者的若干疑問。
第一章“建院之初”簡單介紹最高法院的起源、司法獨立的由來,回顧最高法院當年面臨的艱難境地,解釋大法官為什么拒絕當總統(tǒng)的“法律顧問”。最令我嘆服的是,作者只用了四頁篇幅,就把司法審查權(quán)的來龍去脈梳理得清清楚楚。
第二章“最高法院如何運轉(zhuǎn)(一)”告訴讀者,到底什么樣的官司才能“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交給九位大法官裁判,中間需要經(jīng)歷什么過程,滿足何種條件。換句話說,本章介紹最高法院如何挑選案件。
第三章“大法官”從大法官們的性別、籍貫、信仰、職業(yè)背景、任命方式和彈劾程序,一直談到他們上任后的立場變化。好奇大法官是不是必須讀過法學(xué)院,或者上任前是否一定得有法律工作經(jīng)歷的讀者,可以認真從本章尋找答案。此外,這一章也間接回應(yīng)了大法官“是不是由哪個黨的總統(tǒng)任命,就必須支持哪個黨”的質(zhì)疑。
第四章“首席大法官”側(cè)重談最高法院的“掌舵人”。首席大法官是最高法院里面定調(diào)子的“一把手”嗎?有什么額外權(quán)力?多拿多少工資?不同個性的“首席”,對最高法院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巨大影響?這些疑問,都能在這一章得到解答。
第五章“最高法院如何運轉(zhuǎn)(二)”告訴讀者,九位平均年齡為67歲的大法官,如何在一年內(nèi)審查完8000多份復(fù)審申請,開80多次庭,參加上百次會議,就70多起重要案件作出判決,并撰寫數(shù)百份意見書。
中國讀者可能對第六章“最高法院與立法、行政分支”最感興趣。最高法院與國會、總統(tǒng)之間,到底是“三權(quán)分立,和和氣氣”,還是“針鋒相對,互相掣肘”?司法權(quán)威真可以凌駕于立法大權(quán)和總統(tǒng)特權(quán)之上嗎?作者用一系列有趣判例給出了解釋。
第七章“最高法院與民意”和它回應(yīng)的問題也很吸引人。美國不是標榜司法獨立嗎,最高法院的判決不受國會、總統(tǒng)干擾,但能否遠離民意,或者說比主流民意適度超前呢?最高法院的庭審不存在陪審團,可民意如何體現(xiàn)在庭審環(huán)節(jié)中?在殺聲一片、民怨沸騰的死刑案件中,最高法院如何辨識民意,判定何為“全國共識”?
第八章“最高法院與世界”是最具新意的一章,即使在眾多關(guān)于最高法院的鴻篇巨著中也不多見。本章回應(yīng)的問題別具一格,令人深思:早期的美國人為什么甘做“法律孤島”,排斥外國法律?世界各國又為何紛紛效仿美國模式,建立憲法法院?為什么只有美國堅持大法官終身制?外國法院的判例為何成為美國大法官的判決依據(jù),又如何在政壇引起軒然大波?
最難能可貴的是,盡管這是一本通識讀本,并且因篇幅所限,無法充分展開觀點,格林豪斯作為職業(yè)新聞人的理性客觀還是體現(xiàn)的淋漓盡致。她既沒有刻意神化美式司法獨立,也沒有避重就輕,放棄描述最高法院的復(fù)雜性。在書中,司法理念與運行機制上的復(fù)雜、糾結(jié)之處隨處可見,例如:自由、保守理念之爭對最高法院聲譽的影響;大法官內(nèi)部對憲法解釋方法的重大分歧;大法官終身任職引起的重重爭議;最高法院對庭審直播的強烈排斥;司法機構(gòu)與總統(tǒng)日益嚴重的對立,等等。
化繁為簡地傳播常識,與呈現(xiàn)事物本身的復(fù)雜和糾結(jié),其實并不對立。相反,復(fù)雜本身亦是常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問題上,林達老師有一段話深合我心,她說:“在介紹美國時,切忌走向簡化的頌揚。偏頗的介紹不利交流,反而可能引出幻想,容易在幻境破滅后走向另一個極端,難以冷靜客觀地剖析對方國家發(fā)展中的各類復(fù)雜因素。這絕非交流之道。”在她看來,介紹同一個理念和制度,需要考慮它在不同時間、條件、地點下遭遇的不同困境,強調(diào)制度在歷史發(fā)展和現(xiàn)實運作中的復(fù)雜性。在我看來,格林豪斯這本書,就是傳播常識、呈現(xiàn)復(fù)雜的絕佳范本之一。而我近年之所以為推進法政譯事孜孜努力,也正是為了傳播常識、呈現(xiàn)復(fù)雜。
來源:《人民法院報》2013年7月19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