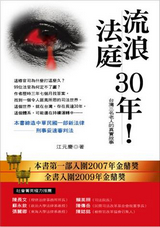�����˷�ͥ30�꣡�����_���������˵��挍���¡�
��Ԫ�c�����_����(d��o)�ČW(xu��)�����磬2008�����
�x�_�_��ǰ��S����Ո�������r�����ᵽ֮ǰ�^Ħ�_���ط���Ժ��ӡ����һЩ����Ć��}�Á�����Ո�̡����ǣ�Ԓ�}����@�_��˾���ƶ�չ�_��S���ڲ������Y��ķ��ɌW(xu��)�ߣ��W(xu��)�B(y��ng)���ҕҰ�_韣���˾������(w��)Ҳ��������^����˽⡣��(j��ng)������f�����_��˾���ƶȵ��\(y��n)����ʽ�����c(di��n)������������׃�������ɱ��ˡ�
����ՄԒ�У�S�����ᵽһ���½�����Ĉ���ČW(xu��)��������(j��)�挍�������ɣ����_��˾���ƶ��д��ڵĆ��}���н�¶�����fҪ���DZ������ҡ����գ�S���ڲ��˰ѕ��́��ˡ������DZ�����ČW(xu��)�������˷�ͥ30�꣡�����_���������˵��挍���¡���߀����һ��ġ�˾���y(t��ng)Ӌ��������˾��Ժ���ɣ����һ�ԣ���(n��i)��Ԕ�и��˾���y(t��ng)Ӌ��(sh��)��(j��)���ęC(j��)��(g��u)�ˆT����������ա��Y(ji��)����(sh��)����(x��)���z��S�����f���@Щ��(sh��)��(j��)���Ԏ������˽��_��˾���ĸ�ò��
�����ɱ����[������ǰ��һ���y(t��ng)Ӌ���һ������ČW(xu��)��һ���ǔ�(sh��)��(j��)�Ķѷe���_�У����ﵫ�ǿ��^��һ�����挍��������������Ӷ����ˡ������L(f��ng)���Į����v���Ĺ���Ҳ����ͬ��Ȼ����������ġ�ģ��䌍��ͬһ�������߸��_���f����ͬһ����IJ�ͬ��(c��)�档S���������@�ɱ�������������������漰����ͬһ�����}����^�����ɱ������֮���Ұl(f��)�F(xi��n)���ڽ�ʾͬһ�����µIJ�ͬ��(c��)��֮�⣬����֮�g�����ϵ��r�����պ͏�(qi��ng)�ҷ������Ҳ���@�����������ˌ�ζ��һ���֡�
���������������ʾ�������˷�ͥ30�꡷�v���ģ������������ˡ���˾���L���г������L�_(d��)��ʮ��ʼ���ϰ��Ĺ��¡���(d��ng)�꣬�@���˾����_����һ�y�и��T����һ�����ڱװ���������Ͷ�����������şo�����������У��Գ����V��ֱ��������o�ֻ�ǣ�������(d��ng)���oՓ���Ҳ�����뵽�����F(xi��n)���x��·;��������D�y���b�h(yu��n)�����l(f��)�r����������(d��ng)���꣬��������ח��߀�����֮�գ����˴������ӡ���(d��ng)����ڽ�ľ�Ӣ���������֮�ģ����˰����������ǰ�̸��T�|�������������(y��n)Ҳ���ܱ�ȫ��ԭ���������ϵ�������һҹ֮�g��׃��һ���������M�^�Ľ^���������������]����������С����܉�������ϰ�����Ŀ�����x�������������\(y��n)�������@��x���SҪ�����_��˾���ƶ�����O(sh��)Ӌ�������������꣬��Ҫ��ȥ��ʮ��Ĺ�ꎣ�
�����@���f�����Ρ��_��˾�������������K���ƣ��ط���Ժһ���ЛQ֮��ԭ���治�����������V���ߵȷ�Ժ���ߵȷ�Ժ�����ЛQ֮��ԭ���治����߀�����V������߷�Ժ��������߷�Ժ����K����Ժ�����ӵ���������ܵĽY(ji��)��������һ���g�����V�����Ǹ��У����dz��Nԭ�У��l(f��)���،����@���N�Y(ji��)����ǰ�ɷN���ЛQ��Ч֮�r������Ҳ�ͽK�Y(ji��)�ˡ�Ω�е����N���β�ͬ�����Ӱl(f��)���،����Q���һ������һ�����ЛQ�Կ����V�������V�ֱ��ö��l(f��)�ظ������t�ߵȷ�Ժ��Ҫ�M(j��n)�и����������������棬߀�����и����������Č�����ˡ�������ȥ��ֱ����߷�Ժ�������V�g�ػ��Ը��О�ֹ���@���������İ��ӣ���(j��ng)����߷�Ժ���l(f��)�ظ�����ʮ���Σ����ڸߵȷ�Ժ��(j��ng)�v�ˡ���ʮ������֮�������ɣ����Ԛv�r���L��
�����@����ጺ�����������ǿ����Բ������˝M�⡣�˂����ܕ���������߷�Ժ����ʲô�ҌҌ����Ӱl(f��)�ظ������@���Ӿ���ô��(f��)�s�y�⣬��횡���ʮ���������ܲ��壿����IJ����ˆ�����ߣ������ڸߵȷ�Ժ��ʮ�������ڡ���߷�Ժ��Ҳ��ʮ��������������ط���Ժ��һ����ǰ��ʮ�ߌ�����(j��ng)�ֵķ��ٶ��_(d��)һ�������˴Σ�Ͷ��֮�ޣ�����զ�࣬��˾��~�ɱ��DZ�횵Ć߀�У��ڮ�(d��ng)���˼����ͥ����˺ĕr�M(f��i)���Ĺ�˾��ȫ��һ����(z��i)�y�����V���ƣ��t�������x�������x����������(d��ng)���ˁ��f���@�������t�����x�mȻ�����fȫ�o���x�����ٴ��˴����ۿۡ�����������?y��u)�˸������������������˸߰��Ĵ��r����Dz��ɱ������⣬����֮���ԌҌұ��l(f��)���،�����������ش����]�в��壬����ˣ��v�θ�����β��ز鰸�������������c(di��n)һһ�ų�������һ���f����������o�ɱ��⣬��β��ܿs�̰�������(f��)���ڣ�һ�νY(ji��)���@���ڹ���˽���y�Գ��ܵ��R����ʽ�V�A��
������Ɔ��}߀���S�࣬����ÿһ�����}�Ļش��ֶ����������µĆ��}���䌍���@���������߮�(d��ng)�����DZ������҂�ͬ�ӵ������^����������������һ���������_��˾���ƶȣ��ѿ��ƺ������ƶȌ�(d��o)�»�և�Y(ji��)���ă�(n��i)�ڙC(j��)���cì�ܽ�ʾ�o������
�������磬�҂����������_��˾��ʷ�ϣ������m�����⣬���Dz��ǹ�������(j��)���߾��Ƶı�Σ�1966����2005�꣬��ʮ���g��ȫ�_˾�����кĕr���^ʮ��İ���Ӌ�ж�ʮ�˼������У���������ӛ���ĵ�һ�y�а������ˌ�����ʮ�귽�Ŷ������v�r��á����^�����Ը����Δ�(sh��)Փ���@������߀���ǵ�һ��1974�������V�ġ��A�����sĸ�������v�rʮһ�꣬��(j��ng)�v�ˡ���ʮ�ˌ������Ŷ�������(chu��ng)�¸����Δ�(sh��)���ļo(j��)䛣�����354-355퓣���
�������ڣ���������dz��B(t��i)������(j��)���ߓ�(j��)˾��Ժ��������Ľy(t��ng)Ӌ��1995����2005�꣬�_��������Ժ���Y(ji��)һ�������Ք�(sh��)��ƽ������һ������������ʮ������һ����һ��֮�g�������Еr�g�Զ̣���������������ʮ������ʮ����֮�g�������Єt��һ��������һ����ʮ��֮�g�������M(f��i)�r��̣������c�����зքe�ڶ�ʮһ����ʮ�������ʮ������ʮһ��֮�g���ЌW(xu��)���u�����@�ӵ�Ч�ʣ������緶����(n��i)Ҳ����������λ�á�Ȼ����ƽ�����Ĕ�(sh��)��(j��)������Ĩɷ�����д��ڵĆ��}���@Щ���}�Ĵ��ڣ��������܂�������(d��ng)���ˣ����������a(ch��n)���Ɖ��Ե�Ӱ푡���飬�������Ǯa(ch��n)����żȻ���������ƶ��ϵĸ�Դ�����Ա��������ĵ�һ�y�а�������
����ԓ��֮����һ�ٱ��l(f��)�ظ�����һ����Ҫԭ���Ƕ����]�������c�������P(gu��n)��������Ҫ�������磬����߷�Ժ���ڵ���ΰl(f��)�ظ����r����ָ��ԓ��������ĸ������Eģ����Ҫ�������Ժ���Ը�����������1988��ġ����匏������1999��ġ���ʮһ������ǰ���ߴθ�������ʮһ�����٣���δ���������ؑ�(y��ng)���@�������飬����������Ҫ��醡��ˌ�������(sh��)��(j��)���r�ҡ����匏���స�l(f��)�r�ь���ʮ�꣬���C������鲻�ס����H�ϣ��������ʮ�������ķ��ٛQ�ĽK�˴˰������I(l��ng)���ֲ�醉m���Ѿõ�ԭʼ�n��������һ��r�g�Ō����톖�}��Q��
�����P(gu��n)�ڰ������ϲ��Q��ԭ������߀�ᵽһ���鹝(ji��)��2005��11�¡���ʮ�������ЛQ������o��֮�z���������V����(d��ng)�r������һ���ּ������������ߺ���љz��ٵ����V���Ɍ�����У����ǵ��ˎׂ�� sһ�o���@�����z��������V�ׂ��½��������V���ɣ��Dz��Ǚz��ϵ�y(t��ng)�ij��B(t��i)���ϲ����������������@�����}ȥ��˾�����Y����ʿ�����б����߾����y�����š����߆����z��������V�����Пo�����r�g���ƣ��õ��Ļش��ǣ����յ��ЛQ��ʮ��֮��(n��i)�����^������(j��)���ɣ��z�������������r�g��(n��i)������V�������V���������a(b��)�͡������V�����a(b��)���Пo�r�ޣ��ش��У�����߷�Ժ���ЛQ֮ǰ�����߲��⣺��֪�����V���ɣ���Ժ��Ό��У���Ի����Ժ�Կɸ���(j��)���ڌ��������������D(zhu��n)ȥ�ߵȷ�Ժԃ���Ƿ��ь������ͽ�����߷�Ժ�����s����֪�������ڙz�������Ҹߵȷ�Ժ�ĶȰl(f��)����߀�����o�Y(ji��)�������߆��к��k��ȡ�ؾ��ڣ���Իͨ�^˾��;�����ن������ПoҎ(gu��)���z��ٷ�߀���ڵ����r�ޣ���Ի�]�С����߿��ȴ��z��ٵ����V���ɣ��v�r���꣬�@�r�������R�����ȴ����IJ�ֻ�������������ˣ����������wϵ���ڵȣ�ԔҊ������35�£���
�����������ܲ��������z��ٲ��ܼ��r��߀���ں͌������V���ɣ��@Щ�����ɞ����۰������еľ��ɣ�����(d��n)�������ġ���߷�Ժ������ƌ���ؓ(f��)��(d��n)�����еġ������ְ����ƶȣ����Ǽӄ��˴˷N�B(t��i)�������@Щ�F(xi��n)��ֱ�ӡ��g�ӵ��cһ�������P(gu��n)���Ǿ��ǣ������ˆT��(sh��)�������L���h(yu��n)����������(sh��)�������L�������ڕ�������������(sh��)��(j��)�͌������茑����ؓ(f��)֮�·���ƣ�ڱ����Ĺ��������澳�r���x֮���˄��ݡ���Ȼ�����H��r���ӏ�(f��)�s����Ɍ������t��Ӱ��ЛQ�|(zh��)��������߀���S�࣬�������������|(zh��)�͘�(g��u)�ɣ����ٵ���������(j��ng)�Ͳ��أ������ɲ�����V���|(zh��)��������߀�з��ɵ������������C(j��)��(g��u)�Ĺ���Ч�ʡ������@Щ���ر˴�(li��n)ϵ���h(hu��n)�h(hu��n)��ۣ���(g��u)���˕�������ʾ�ķN�N���}���ɵı������@Щ���}�Ĵ��ڣ�ֱ��Ӱ푵��_��˾��������Ŀ�еĹ�������
����S��������1985���1995��ɶ��M(j��n)�І����{(di��o)�飬�l(f��)�F(xi��n)�_��˾���mȻ�ڲ���ĸ���乫����������Ŀ�е�λ�Ås������䡣�����ڱ�����������漰�̰������Ƿ�����ŷ�Ժ�IJ����ǹ����ģ����r��ǰһ���{(di��o)�飬�_���б�ʾ���ŵ����аٷ�֮ʮ���c(di��n)�ģ��_���h�аٷ�֮��ʮ���c(di��n)�塣��һ����ȫ�_�����{(di��o)�錦��r���@����(sh��)�־ͽ����ٷ�֮���c(di��n)�����D(zhu��n)Ҋ�ֶˣ�2010���������ڴ˱���֮�£�˾���ĸ��ٴγɞ鳯Ұ�p���Ĺ��R��Ŭ��Ŀ��(bi��o)��1999�꣬��������������Ρ�˾��Ժ��Ժ�L�ăxʽ��������ʩ����ᘣ����У�������˾����������������λ���˺��ڲ�ͬ���ϣ��������Ҍ��Լ���˾���������аl(f��)��ӛ䛿ɲ��ߣ���(j��)�������߽y(t��ng)Ӌ���_(d��)��ʮ�˴�֮�ࡣȻ�t���Ξ顰˾��������(j��)���ϱ����U�������ǡ�˾���Ǟ��������Ҫ�����ڡ�������������������֮����ȫ�w�������е�Ԓ�U�����⣺�����Ұ��^���κ�һ���Q�������������g��ƽ�����x��һ���֣��@���҂���؟(z��)�Σ�Ҳ���҂��Ęs�u(y��)����������142퓣�
�����@���鹝(ji��)����Ҹ��dȤ�ģ��o���ǡ�˾�������Ǿ�Ԓ��������^ȥ��ʮ������{�@߅˾���纰����푵ģ�Ҳ���ǡ�˾�������@����̖��ͬ���Ă��h�֣������ڵı�������(n��i)��ĺ��x���Ю�����ͬ����̎�����@ͬ����֮�g��
�������һ���ڱ��������A��W(xu��)���W(xu��)Ժ���v�r��S���ڿ��Y(ji��)�_��˾���ƶȰl(f��)չ�v�̣���������£�1945��1979��顰���I(y��)�����r�ڣ������c(di��n)�����϶��µ��ṩ����˾��Ʒ�|(zh��)�����҂���Ϥ��Ԓ�f���@��˾���I(y��)�����A�Σ�1979��1994���������^�����⻯���r�ڣ��@һ�r�ڣ�������˾���е�؝�����}�õ���Q������_��������������ܴˆ��}���_��1994��1999�������^����(d��)�������r�ڣ�����Ҫ��(bi��o)־��ͨ�^1997����ޑ����骚(d��)����˾���A(y��)���ṩ���ϣ�1999���Ժ�˾���M(j��n)�롰��������r�ڣ������^�������������Ҫ�������ڌ��I(y��)��(n��i)���ĸĸּ���Ƴ��M�����I(y��)���A�����棬���˾���������ؓ(f��)؟(z��)�̶ȣ���˾������֮�fҲ�ɴ˶��d��S���ڮ�(d��ng)����ԡ�˾���ĸ���ٸĸ���}����һ���������ڷ��Ɍ��I(y��)ҕ�ǵķ��ɸĸ�������u�����f����˾���ı��|(zh��)����һ�N�M���������x�еăxʽ�����F(xi��n)������ķ��ɣ�����һ�N�߶ȷֻ����ƶȣ���Ȼ���䌣�I(y��)�ϵ����_�ԣ������@�N���_�Բ���Ψһ�ġ�˾����횵õ��˂�����ه����t����ʧȥ�˴��ڵĻ����rֵ��������148퓣����@���Կ���S���ڌ���˾�����������ԏጡ�
����˾��Ҫ����(w��)�����M���������Ҫ���õ�������J(r��n)�ɺ���ه�����@�����⣬�ɰ����ԡ�˾������(y��ng)��(d��ng)��ȥ���h(yu��n)��Ȼ�����ɰ�˾���ƶ���̎�ڰl(f��)չ�IJ�ͬ�A�Σ������c������ӵķ�ʽҲ������ͬ����˾������һ�Z�ڲ�ͬ�Z���еľ��w���x���M��ͬ�������f������ꑵ�˾�����ڌ��I(y��)��;�С��ڴ˱���֮�£���(qi��ng)�{(di��o)��˾������������s˾�����I(y��)���M(j��n)�̣�߀Ԣ�мӏ�(qi��ng)��˾��������Ӱ�֮�⡣��ˣ���˾�����Ŀ�̖��ÿÿ�ò���������푑�(y��ng)���������Р��h���䌍������˾���������ã�˾������(w��)�������ҿ������@�ӵ�����o����(d��ng)��Ҫ���Ć��}�ǣ����Ӳ�����˾��������β�������˾�������LjԳ�Ⱥ��·����߀���ߌ��I(y��)����·�ӣ��Ƿ�Գַ��ɵ������ԣ����ӵ��ƶȰ����܉��C˾����������������Ч�ʣ�ʲô�ӵ�˾���ƶȸ��ܝM������l(f��)չ����Ҫ���õ������(sh��)����ه����˼���@Щ���}�r���҂����l(f��)�F(xi��n)�������˷�ͥ30�꡷����ʾ���_����(j��ng)����Щ�������Y���b��
�������磬�oՓ���_��߀�Ǵ�ꑣ���˾�������Ǐ������F�������Ҫ�Գ��@�ӵ��������Ҫ�M��һ���l�����Ǿ���˾���ƶȽ����ęz���u�С���ˣ�����˾���ƶȵĹ��_�����YӍ�_�ţ����S��˾�������ɵ�����̽�������u���Ȟ���Ҫ�������˷�ͥ30�ꡱ֮Ĺ��£��ڴ�ꑲ����ܳ��F(xi��n)���ͺ����_�������С����L30�ꡱ�Ĺ��¡����^������Ҫ�IJ�ͬ߀���ڣ������˷�ͥ30�꡷�@�ӵĈ���ČW(xu��)��Ʒ�����@��ɴ��o�ɮa(ch��n)������飬�@��Ҫ�@�������˾�������Y�Ϻ��y���܉��_�\(y��n)���@Щ�Y�ϸ��y�����Ҳ������Ҫ�ģ����ǘӌ�˾�����ٸ�����̽����ֱ�����ܵ����u��������DZ���ȫ���^���ض��ܵ��O�����ơ��@����������@�N̽�������u���`���ģ���������������@���ǘӵġ������_�����\Ȼ���������䱾�����ء��Ϸ��c���������v�����_�c�����ǣ�����������ܴ_����������λ������Ξ鷨���ϵę�(qu��n)���ṩ�Ԍ����ϣ�
�������f��˾���c���ε��P(gu��n)ϵ���@���ǹ��϶����µ�Ԓ�}���^ȥ�������F(xi��n)�ڣ��S�������ţ����ɣ���(d��ng)ȻҲ����˾����������ȫ�c���ν^�������H��ˣ��������ţ�һ������ķ���ֻ�������������صה[Ó����Ӱ푣������ǬF(xi��n)���ģ��Ǖr�������^���Ρ�Ȼ�����������S��l(f��)�_(d��)�����ƶȵĽ�(j��ng)�s�C���@�N������һ�N������뷨���_���Ľ�(j��ng)�ͱ�����˾���Č��I(y��)�����M(j��n)�����ɵ������ԣ��mȻ��F(xi��n)������l(f��)չ����Ҫ�������@ЩĿ��(bi��o)�Č��F(xi��n)�������ܽ�Q���І��}���������������Ć��}�������������c�����P(gu��n)ϵ�Ć��}��Ҳ������˶����⡣�䌍����˾�����������������Ͱ�����������ζ�����Ǵ����A���W(xu��)Ժ�����v�У�S����Ҳ�ἰ�@����������Ć��}����ָ����˾����(d��)���鷨�������裬��Ȼ�o�ɱ��⣬����˾���c���ν^����Ҳ��(d��o)���䌦��������x������ؓ(f��)؟(z��)���@�r�����λ��ě_�����_ʼӿ�ӡ���(d��ng)Ȼ���@��һ�N�V�x�����λ������@���A�Σ����ε��ⲿ���A(y��)�ѽ�(j��ng)���ų����⣬���ǣ�˾��֮�������ǪM���Č��I(y��)��Ŀ������õ�ij�N���J(r��n)��
�����@��ʲô�����Εr����˾�����λ����@�N��������ì�ܵı������ܳ������Ǐ�(f��)�s�����B(t��i)��(y��ng)��(d��ng)������⣬���еķִ��֮�(d��ng)����������˷�ͥ30�꡷���Ќ�����һ��������һ�Ό�Ԓ���o�҂��ṩ��һ���H�߆��l(f��)�Ե�˼������
����2005��8�£��_���ߵȷ�Ժ��һ�����֙�(qu��n)���������ЛQ�����l(f��)�����푡�ԓ���У�ij�������ͬ�W(xu��)�������гɹDz�ȫ�Y���Q���������ޡ��������ͬ�W(xu��)ȥ���w���n�r������ݝ��������ͬ�W(xu��)������֮���ͬ�W(xu��)���L��Ժ�����֙�(qu��n)֮�V��Ҫ��ԓ�W(xu��)У�����ͬ�W(xu��)�o��p���r����һ�������J(r��n)�飬�ͬ�W(xu��)�������ˣ��ҟo�C��(j��)�C�����й�����^ʧ������ЛQԭ�攡�V�����ڶ����r����Ժ�J(r��n)���֙�(qu��n)�������ЛQԓУ���ͬ�W(xu��)��ͬ�r���Ӌ���_�����ٶ��fԪ������һ��(j��ng)����������WȻ���|(zh��)�ɡ����u֮��������ָ�����@һ�ЛQ���ԡ��ڰ��������˓�(d��n)�Ĵ�һ�ЛQ���ݚ�����rֵ�c�����������鲻֪���ԓ��ν̌�(d��o)�W(xu��)�����˶��������ڽ̽���@�ӵ��ЛQ������������������������������������������ޡ��ļ��L���t��(d��n)�Č���]�����ٸ�?gu��)��������ĺ��ӡ������������u��ì�^����ָ��ʹʧ���ӵ�ң������ʹ֮�࣬�Qԩ��ֹ�������J(r��n)�飬�@һ�¼��У�ԭ�桢���漰˾������������ݔ�ң�����149-150퓣���
��������@�N���ºͷ��ɵ������҂�����İ�����e�ǣ��@�N�������γɼ��ǬF(xi��n)����������һ���֣�ͬ�r�ֺ��A�����������Ļ��������P(gu��n)���挦���ݛՓ�����Ķ��������U���䷨���˵������r�f����һ���˿��]�����������ٿ������Ƿ����飬Ҫ�ѷ��ɔ[�ڵ�һλ����������Ќ��С����ڷ��ɡ���ͬ�r��Ҳ���J(r��n)�����]�ϵ��ЛQ����������ô��ě_������������150퓣��@�䡰�]�ϵ��������������˷����c������˾���c������������x�c��(j��ng)�����е����x֮�g������c���u��Ҳ��¶����(j��ng)����ֲ;�������F(xi��n)�������ƶȵ��A����������R���������y�������������@�ӵ�����c���u��˾���Ĺ������ųɞ醖�}��˾��������������@����Ҫ�ͱ�Ҫ����ô�����������܉��@һ�������@һ���u�����F(xi��n)��˾�����������أ����߽o�˃ɂ��֣����ģ�Ԕ��������20�¡����ij�Խ���ɡ������@���ش���̓�������ھ��w�Z����(d��ng)�У��sҲ���ǟo�E�Ɍ���2007��8��23�գ��v��(j��ng)����ʮ�������ĵ�һ�y�а����K���ڡ���߷�Ժ���K����ח�������м�(x��)���x�@�ݽK���ЛQ�����c�v���ЛQ����գ��l(f��)�F(xi��n)�����o���ЛQ�ġ���ʮ���������]�н�Q֮ǰ�ѽ�(j��ng)����߷�Ժ��ָ�������І��}��������o������ڂ��e���}�ϡ����o��©�������ǣ�����߷�Ժ���s������^�@Щԭ���܉�����������һ�ΰl(f��)�ظ����Ć��}���D(zhu��n)����ȡһ�N��(y��n)��ķ��Ɍ��������ԙz��ٵ����V���ɲ��Ϸ���Ҏ(gu��)�������g�ء���ʲô���@�ӣ������ڵڶ��졶�Ї��r�����P(gu��n)������ҵ��˴𰸡��@�t����ָ�Q�����hͥ�J(r��n)�鱾���p�A����ʮ�꣬���������ஔ(d��ng)��ĥ�������]�аl(f��)�صČ��棬��˾S�ָ�ʮ�����o���ЛQ�����ߵĽ��x�ǣ����������˚v��(j��ng)����ʮ�����ĥ���K�چ��ٵ����ģ��Ƿ��ٵ����ij�Խ�˷��ɣ��ŵ��ԽK�Y(ji��)�˰�����������278-279퓣�
�������@����������һ̎������ӛ���˕r���_�����L���RӢ��1999��ͬ����ɽ��(chu��ng)�k��ʥ��(y��n)�����vՓ���c˾���P(gu��n)ϵ��һ�Ό�Ԓ��ʥ��(y��n)�����f������(zh��)��һ��Ҫ�дȱ����c�ǻۡ�����顰���������ģ����ǻ�ģ�����]���Դȱ��ā��(zh��)�������ܾ�����(zh��)���������������ˣ���ʹ������y������]�����ǻہ��(zh��)�����Д�Ҳ���ܕ��e�`�������J(r��n)�飬��(y��ng)�����`���^�c(di��n)��Մ���ɣ����`���^��ͷ��ε��^�(y��ng)��(d��ng)��������c�ںϡ�������ӆ�����(zh��)�����ط�����Ҫ���Л]���ǻۣ��Л]�дȱ��ġ������ˣ����W(xu��)�����������_������(w��)���L���RӢ�Żؑ�(y��ng)�f������(zh��)����Ŀ����Ҫ�S�o(h��)��ƽ���x�������ڈ�(zh��)�з��ɵĕr���e��Ҫ�дȱ����ǻۣ����܉������ǡ����̎������ͬ�r�ָЇ@���_���ķ��W(xu��)������Ƿȱ���ĵ�Ѭ�պ��Ⱦ��������ķ��ɿ�ϵӖ(x��n)�����ܶ෨�Ɍ��I(y��)�˲ţ����s�]�k�������B(y��ng)�������ǻ۸��ȱ�������ֻ�������˷��١��z��١��Ɏ�֮�������ҵ��X��ͷ�ʡ����֪��Ҫ���B(y��ng)�������B(y��ng)������������Ժ������������J(r��n)�鷨���c����һ����������Σ��˂������`�t�����Σ��������ڽ̵���أ�����253-254퓣���
�������`�c˾�����ڽ��c���ɣ��@����һ�����϶����µ�Ԓ�}���F(xi��n)������l(f��)չ����Ƽ����£������ܰ��@Щ���}�����ڟo�Ρ��෴���F(xi��n)������ֹ���(x��)�ܣ��ƶȷֻ�����ʽ���Ի��̶Ȳ���������ÿÿ������`�c�ƶȃ����g��Ó��(ji��)���������еľo���P(gu��n)ϵͻ�@�����������˷�ͥ30�ꡱ�Ĺ�����һ�����������������ޡ�������һ��������ǰ�����ɸ߶ȷֻ������I(y��)��Ҏ(gu��)�����ƶ��С��������a(ch��n)���Ļ�և�Y(ji��)�������߄t���I(y��)�ărֵ�^�����x�^�c���˵ărֵ�^�����x�^��������_ͻ���@�F(xi��n)���@�ɷN��r���p���˷��ɵ�����(d��ng)�Ժ�˾���Ĺ������������������ɵ����Ρ�Ҫ��׃�@�N��r���Α{�ƶȲ�������ƶ����˽��������ˈ�(zh��)�У����˶����ڡ������ƣ�ͽ�����������С�Ү�d�f���ɷ����˶������@�������������ɿ��Ԟ����˵���Ҫ�����׃�������f��ֻ�а��ʡ��ۡ��ȱ�����֪��ע����������(zh��)�����÷��ĸ����h(hu��n)��(ji��)��ֻ������ȥ�I(l��ng)�����ɵľ�����ķ��l���Мضȣ����˸���ƶȲ����������҂����������е�����ŕ�׃�ÿɐۡ�
�����҂��������@�ӵ����x��ȥ���⡰˾������
��Դ���Ϻ����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