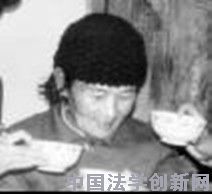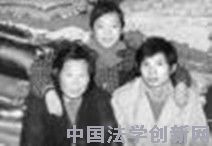我們的經歷,具有不可復制性,它既是一種磨難,
也是上蒼賜予我們的一筆寶貴的財富
祖母和祖父
祖母的特點就是喜歡說,喜歡嘮叨,這樣,肚子里郁悶、痛苦就能不斷地渲泄出來,
因而作為老病號的她,得以90歲高壽謝世
感情篤深的祖父祖母
在我祖父年幼的時候,很可能我們這個家族已經開始衰落了,所以曾祖父就給他起了“鴻興”這個名字,以希望家境能夠興旺一點。迫于經濟壓力,祖父在十二歲多一點時,就被送到上海城里一家工廠做學徒,能夠自己養活自己了。
祖母家姓蔡,原來也是一個小康人家,這從她名字“金英”中也能看出。但到她出生時,家道也已經破落,在她6歲時,就托人打聽誰家需要童養媳。恰好我曾祖母和她們家素有來往,看到祖母盡管穿衣很破舊,但長相還很端莊,就收留了下來。沒有想到的是,祖母后來不僅越長越漂亮,而且個子還超過了祖父。
祖母是否真心喜歡祖父,我不清楚,因為后來我問祖母這個問題時,她總是說:人家把我養大了,我能不嫁給他嗎?不過,祖父卻是真心喜歡祖母,一切事情都聽從她的,非常寵她。
每年休探親假時,不僅家務活全包,就是祖母的所有衣服也都是祖父洗的。這在重男輕女的那個舊時代,還是非常不容易的,足見祖父用情至深。
祖父原來在上海的一家香煙廠里做鉗工,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時每月收入為四個大洋,他說這點錢省著用,不僅可以養活全家,而且可以節省下一點,積蓄幾年還可以蓋間房子什么的。
我當時聽了,也沒有什么感覺。后來讀了大學,接觸到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收入,知道當時北大一個教授的月工資收入是三百多大洋,講師幾十塊大洋,就是青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做臨時工,也有八塊大洋的收入。這樣一比較時,才知道當時知識分子的收入是多么高啊!相形之下,工農聯盟家庭的經濟境況只是可以解決溫飽而已。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祖父還在上海。過了兩年,就業形勢不好,我父親找不到工作,祖父就將自己的工作崗位留給了兒子,和幾個朋友一起去了天津。從此,一直到退休,他就孑身一人,遠在天津工作,幾十年來上海、天津兩地奔波,人很辛苦。
祖父由于工作努力,表現突出,也擔任了廠里的一點小職務。一邊工作一邊讀夜校,文化水平大概達到小學四年級吧,可以給祖母寫信了。但因為祖母不識字,故寫來的信,都是由母親、嬸嬸看后轉述給她聽,我們孫輩上學后,就由我們代看代述了。其他內容不太記得了,第一句話是記得很清楚的,就是“金英吾妻,你還好吧……”
熱情的祖父和病弱的祖母
祖父個子瘦小,但精力充沛,性格豪爽,為人熱情,極講義氣,所以朋友一大幫子。他的熱情可以用一件小事來說明。我小的時候,有一次他帶著我到鎮上,在路上走著走著,突然他的身體像子彈飛出去一樣往前飛奔。等我反應過來時,他已經奔出去了二三十米。仔細看時,原來前方有一個人推了一輛自行車上橋,自行車上裝滿了東西,很重,快到橋頂時,推不上去了,僵在那里,很是危險。祖父奔過去就是要幫助他推自行車。
祖母原來身體還行,但可能干農活太過于辛苦,到四十多歲時身體就垮了,每天都要吃中藥,田里農活也干不了,只能做一點輕松的家務活。祖父盡管寵愛她,但一年也只有十幾天的探親假,平日照顧不到她。她的生活孤寂、心情郁悶這是常有的事。
好在她性格開朗,喜歡嘮叨,積壓在心里的苦惱能夠及時渲泄出來。我讀大學以后,每年暑假、寒假在家里看書、寫東西時,她就坐在我的身邊,和我嘮叨家里和村里的事,一件事也許要說上幾十遍、上百遍,也不管我是否在聽。上下午各嘮叨一遍,完事后就心滿意足地去忙她自己的其他事了。正是這種外向的性格,祖母最后也活到了90歲的高壽。
我的父親
懦弱的父親和堅強的母親,在23年的分居期間,
每年在一起的時間也只有短短的14天探親假。
下放回到農村
我父親小時候,因為身體單薄,干不了農活,到16歲時,祖父就把他接到上海城里,跟著自己學鉗工,當學徒。快學成時,剛好趕上上海解放,臺灣的國民黨和西方列強對中國內地實行封鎖,城里工作不好找,祖父就把自己的工作崗位讓給了我父親。父親成家后,在上海廠里工作,母親在農村干活,倒也太平了幾年。
但1958年“大躍進”以后的三年困難時期,城里商品糧不夠吃,農村第一線的勞動力又不夠。到1960年前后,不得已國家開始實行減員簡政,動員部分在農村有家屬,人民公社有地耕種、有農活可干的在職工人,尤其是黨員積極分子,帶頭回到農村勞動。
這一政策從1960年起,中央開始醞釀,到1961年開始實施。1961年全國減少了城鎮人口1300萬,1962年,又繼續減少1300萬。其中,除了部分家屬之外,70%以上都是在職職工。當時政府決定,1958年以后新進廠的工人就是重點動員回鄉的對象。父親雖然不屬于這一類,但因為我們老家在農村,祖母和母親都在鄉下,所以廠里的領導就不斷地動員父親回到鄉下去。
當然,這種回農村,即使在當時也是自愿的,并不太強迫。如果當事人堅決不同意,領導也沒有辦法、不再強求。當父親第一次領了表格,和我母親商量時,母親沒有同意,主要理由是父親身體單薄,人又瘦小,從來就沒有干過農活,不適合在農村生活。而他的鉗工技術,在廠里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是八級工,這是工人中最高的技術級別了。母親說,工廠才是你的家,你不要回來。
沒過幾天,廠里的書記、廠長又做父親的工作,說你是中共黨員,又是廠里的工會主席,你應當帶頭響應上級的號召,回到農村。實際上,我們幾個領導也都報名了,我們也都要回到農村去了,你考慮一下,帶個頭吧。父親想想,書記、廠長都報名了,自己再不報名,顯然不夠積極,與一名共產黨員的標準不符合。所以,就再次去報名,領了表格。這次他吸取教訓,不再和母親商量了。等到母親知道,父親已經辦完了全部手續,由廠里派人送回鄉下了。
“一點農活都不會”
母親為此事大哭了一場,也大鬧了一場。但事已至此,也沒有什么辦法。回到農村后,果然不出母親所料,父親一點農活都不會干,不僅身體吃不消,而且也沒有掙到多少工分,我們姐弟三人都在讀書,開支不小,家里的經濟捉襟見肘,出現了問題。
尤其是后來母親打聽到,父親廠里的書記、廠長,并沒有下鄉,廠一級的干部里只要有一個名額下鄉,上級下達的下放任務就算完成了。而父親作為工會主席,也可以算作廠級干部。得知這事后,母親更生氣,經常和父親吵架。而父親人很懦弱,只是拿個小凳子,默默無語地坐在墻角里,聽著母親數落,從不回嘴。
母親事后和我說,她和父親此后經常吵架,就是從這件事開始的,她主要怪父親在這么大的事情上沒有和她商量,而且人實在是太老實了,沒有一家人如何過日子的觀念。父親輕易放棄城里工作,回到農村,讓祖父也很失望,因為祖父去天津工作,就是為了讓我父親在城里有個工作,不致失業,可不曾想到最后還是丟了工作。
當然,母親吵架歸吵架,內心還是很心疼父親的。看他實在無法勝任農村的勞動,就建議父親發揮所長,以鉗工技術,做些手藝活,如自制煤油燈出售,幫鄉親鄰居修理鋁鍋,磨剪刀,修理鐘表,等等。這樣,父親就挑起了擔子,走街串巷,攬些小修理的活兒。掙到的錢盡管不多,但比單純干農活要好許多。
但這種日子畢竟辛苦,家里經濟也不見有大的起色,所以當1962年國家經濟形勢開始好轉后,上面下來政策,說像父親這種“下放工人”,在國家建設需要招工時,可以優先照顧。說是這么說,由于父親太老實,從來不肯去找生產隊和大隊領導說自己的事,故一直也沒有機會重新回城再就業。
拖到1963年,當時下來了一個去青海軍工企業(保密單位)的招工名額,一方面政治要求極為嚴格,一般的下放回鄉工人都不太符合這些條件,另一方面許多人嫌那里實在太遠,太艱苦,不太愿意去。這樣,大隊上想到了父親,把他報了上去。各方面條件都符合,父親終于離開了讓他傷心、郁悶的地方。
父親的企業,因為是保密單位,所以寫信、寄東西等,都是用多少號局、多少號信箱,我們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過了兩年,父親又被調往四川廣元的深山溝里的一個軍工企業工作,聯絡方式也仍然是一串阿拉伯數字的單位地址。親戚們有時好奇,問他在里面做點什么,是什么工廠,他嚴守秘密,從來就不說。一直到他去世時,有一次我無意中講起此事,他仍然不吱聲,只說了一句,我向組織上保證過的,永遠不能說。
父親的艱辛和愛
父親身體盡管單薄,但原來體質還是可以的。然而,可能長期在深山溝里工作,新鮮的蔬菜吃得少,因為缺少維生素或其他因素,到50歲時,他的健康狀況就直線下降,又是冠心病、又是腸胃炎、還有肺氣腫。1985年,父親55歲,終于等來了可以辦理病退的機會,回到了上海。此時,我已經留在華東政法學院工作,弟弟也已經考上了第二軍醫大學。本來指望父親可以安享晚年,不幸的是,退休才過了5年,父親就因患癌癥去世了。
每每想到父親1963年去青海,1985年病退回到上海,和母親分居長達23年,每年只有14天的探親假可以和家人團聚,年紀不大又離開了我們,真的是很辛酸。他在廣元工作時,回上海的火車要走兩天兩夜,軟、硬臥票不用說了,就是硬座票都是沒有保證的。有幾次他是一路站了48個小時才回到廠里。但他對此從來沒有發過牢騷,總是說,比他還苦的人世界上多得是,他并不是最苦的。
父親去世后,我和弟弟也曾推測過,父親做的可能是我國核試驗的工作。因為不僅是父親,他的幾個同事,也是在退休前后55到60歲之間去世的。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后,我注意到報紙上的報道,說四川廣元的山溝里,有核設施企業。當然,這只是推測而已。即使父親在這一廠區里工作,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父親老實巴交,沉默寡言,性格又很懦弱,總是受人欺負。但他人非常聰明。他在工作之余,就會畫一些人物肖像,貼在墻壁上,自己欣賞。我記得即使他被下放農村、人生最為落魄時,也沒有放棄這一愛好。他畫的劉邦、項羽和韓信等,貼在墻上,栩栩如生。可惜的是,老家動遷時,這些畫都沒有能夠保留下來。
父親一生最感自豪的就是我們幾個兒女,我是學法律的,弟弟是學醫學的,姐夫當時是農村里的干部,后來也出去讀了大學。父親不善于表達情感,但每次我看到他時,從他滿眼的愛意,我已經讀懂了他感情的全部。
反抗舊中國的思想根基
父親生前盡管吃了不少因為老實處事而帶來的苦,但他從來不怨政府、不怨他人,這主要源自他對新中國的認可。他一直認為新中國比舊中國要好上許多倍,尤其是在社會秩序上。在他不多的話語中,曾和我多次講起過他的堂姐,即我的堂姑的故事,讓我知道了他厭惡、反抗舊中國的思想根基。
20世紀40年代初,父親當時十來歲,上海郊區的社會秩序是很混亂的。當時不僅有日本軍隊駐扎,汪偽軍橫行,就是土匪欺壓老百姓的事,也不絕于耳甚至是駭人聽聞的。我的堂姑,長得非常漂亮,嫁給一姓張的小康之家。堂姑父的妹妹15歲那年一次出去趕集,被我們那里的一個土匪頭目“小大班”看到,當天晚上就拿了手槍,跑到張家,把她給奸污了。
堂姑父和堂姑出來阻攔,不但沒有成功,反而惹上了更多的禍患,年輕貌美的的堂姑反被“小大班”盯上了。第二天晚上,“小大班”又帶了幾個人來,強暴了堂姑。堂姑夫上去阻攔,被“小大班”手下的人打成重傷,落下了終身殘疾。
父親每講到這里,總是說,在那個年代,稍微長得端莊一點的姑娘,一般一個人是不敢在外面走的,也不敢拋頭露面,而現在新社會,真的是太平多了。你看你姐,長得漂亮,隊里有幾個小赤佬(男青年),曾想到我們家的后窗口偷看她洗澡,被你母親發現,出去一頓臭罵,下次再也不敢來了。可能父親的這種經歷以及認識,正是支撐他承受了諸多人生磨難和痛苦的力量,也是主導他堅持熱愛新社會的思想信念吧。
想念我的母親
母親留下的照片不多,這是僅有的一張母親和我及女兒的祖孫三代合影,
雖然已經過去了20年,但仍給人以非常溫馨的感覺
堅強的母親
和父親比起來,母親的個性要堅強得多。她出生于1929年,比父親大一歲。母親的特點首先是心腸特別熱。生產隊里的人,不管是哪一家,遇到點什么困難,只要她能幫得上忙的,她一定會想方設法幫助人家。當時的農村,和現在一樣,糧食、蔬菜等不太缺,最缺少的是現金。人民公社實行工分制,平時干農活,每天計工分,到年終計算一個工分折合成多少錢。因此,家里如果沒有人在外當工人,平時里遇到小孩上學、老人生病等,需要用錢的時候,就比較窘迫,只好四處借錢。
雖然我們家也不富裕,但當別人問母親借點錢時,她二話不說,只要手頭有,都是來者不拒,立馬就給人家。即使有人借了以后還不了,或者“忘記”還了,她也不太在意。“只要別人求我,頭當夜壺也肯”(就是“為朋友可以兩肋插刀”的意思),這是她經常對我們講的一句話。正是母親的熱心腸,贏得了別人的尊重。母親的言行,也教育著我們:一個人活在世界上,只有真誠地不斷幫助他人,才能體會到幸福。
母親的勤勞,也為當時生產隊里的人所稱道。由于父親長期在外地工作,我們姐弟三個都由她一個人撫養帶大。母親每天一早起,先在生產隊里拼命干活掙工分,收工后在家里的自留地上種菜種雜糧供應每天吃的,天黑后回到家里,還要張羅著為我們三個孩子做家務,日子過得很是辛苦和艱難!然而,正是她的辛勤勞作,才有了我們三個孩子的健康成長。母親用自己的行動,無聲地啟迪著我們:一個人只有勤勞地工作,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母親的缺點是性子很急,當然,脾氣也不好,看著不慣的人和事,就喜歡說,有時甚至還要罵人。這樣,就出現了本來因為樂善好施,弄得好好的人際關系,被她這么一說、一罵,反過來又鬧得很僵。事后她雖然很后悔,但脾氣總是改不了,下次遇到這類事時,罵人的老毛病又會重犯。這種情況,直到我們三個小孩慢慢長大以后,才有所緩和。
永記母愛
后來,政府要修建上海市區通往浦東機場的龍東大道,我們村就被征用,社員們沒有了土地,母親就和大家一起,享受政府所給的生活補貼,她和鄰居們沒有什么事干了,也沒有什么利益沖突了,就經常在一起搓搓麻將,聊聊天,過去的不愉快也都煙消云散,老人們的關系倒真的變成其樂融融了。
或許因為青壯年時期實在太辛勞了,以至于上了年紀后,母親患了帕金森病,身體一下子就不行了,但她仍然堅持著與疾病抗爭。直至在生命的最后兩年,她癱瘓在病床上,不僅無法起來,而且身上還有三個碗口大的褥瘡,有一個褥瘡甚至已經爛至骨頭,天天折磨著她。每天換藥時的疼痛,我們在邊上看著都無法忍受,而母親卻極其堅強,從來不叫喚,也從不呻吟,默默地承受著這一切。
2009年母親去世,與先她而去18年的丈夫、我的父親在天國相聚了。作為一名普通的中國農村婦女,一輩子在黃土地上勞作、耕耘,別說沒有上過電臺、電視臺,就連片言只字也沒有留存在報刊雜志上,就這么靜悄悄地走了。中國極大多數的勞動婦女,都是這樣默默無聞地在為中國的建設、繁衍中華民族的后代,而辛勤地勞作著,母親只是其中的一員而已。我想,謹以此小文,獻給母親,以及所有的中國勞動婦女,你們的貢獻,我們,你們的子女,都是銘記在心的。
(節選自《火紅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