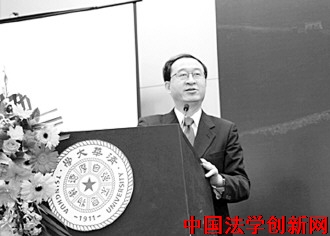■ 本期嘉賓 ■
主講人: 季衛東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
點評人: 俞可平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張維迎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王晨光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 法制日報記者 蔣安杰
中國近代最早的法學不僅包括現在的狹義的法學,還包括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社會科學,清華大學法學院第一任院長陳岱孫先生就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那時的法學是名副其實的“大法學”,對培養學生開闊的視野、合理的知識體系發揮過重要作用。
11月20日,中國法學會和清華大學聯合主辦、法制日報社協辦,中國法學會法律信息部和清華大學法學院承辦的第4期中國法學創新講壇上,來自政治學、經濟學、法學三個領域的四位嘉賓同臺共話“推進法制的新程序主義進路”,用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教授的話說,很容易讓人回想起當年“大法學”的盛況。
四位同有北大背景的學者,季衛東教授北大法律系79級學生,評論嘉賓俞可平教授北大國際政治系85級學生,張維迎教授94年回國到北大,王晨光教授本碩博均就讀于北大,機緣巧合地因為法治的主題同臺交流,讓近三百名聽眾對參與的論壇充滿期待。他們的觀點是否共鳴?他們的觀點是否截然不同?
季衛東:在價值沖突中實現共識
當這個社會多元化,有不同價值觀的時候,我們不能強調某一種特定的價值,我們要強調不同的價值能夠共存、能夠就公正事務達成制度的條件。如果我們僅僅強調特定價值的話,結果有可能造成某種不同形態的壓力。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我們要追求共識,我們要追求一種和諧社會的話,程序正義必須有一些價值。
舉一個例子,很多人都覺得上海非常漂亮,如果我們問,你愿不愿意住在這樣一個城市里,很多人都會說愿意。但是這一過程中難免會發生一些價值沖突,例如城市化建設與被拆遷者的權益保護。雖然城市化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但卻不能忽視被拆遷者的權利。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一種價值觀,哪怕再好、再有道理,當把這種價值觀絕對化的時候,都會有問題。這時候,重要的是不同價值觀之間的平衡,以及在不同的價值取向中如何達成共識。反過來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利益集團、不同價值觀之間的博弈,他們的價值兌換和辯論,以及圍繞不同主張的說服力競爭,就會成為公共事務決定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結果自然會導致對民主程序的要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是一個好東西,民主是一個價值判斷,但是民主決策程序本身是沒有價值的。任何一種價值,只要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只要有足夠的說服力,同時也能適當照顧到少數者、個人的價值觀,這個決策就能夠有正當性,就能夠得到遵守和產生實際效果。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程序成為解決我們現實問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在一種公開透明、平等的空間中讓不同的價值觀進行表述和格斗,最后博弈出一個比較正當的決定。
在我國這樣一個本來就過于強調實質性價值文化傳統中,在這樣一個具有太大的多樣性的社會里,如何才能實現各種不同價值觀的平衡呢?我們要做的就是“和”而不同。我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價值觀是多元化的,但是缺乏制度性的保障。
在這樣一種多元化情況下,很容易造成分裂局面,盡管價值觀“和”而不同,但是當某種價值觀壓到其他價值觀的時候,當價值觀之間調和的均衡失去的時候,必然會造成分裂。因此,法律總的趨勢不是強調某種特定的價值,尤其在中國社會多元化、市場化程度已經達到如此的地步,更應該強調不同價值之間的共和。
我提出新程序主義和過去的程序主義有什么不同?過去談程序的時候往往強調的是形式,我們知道在二十一世紀以后,整個世界的變化已經越來越難以按照形式、法學家所設想的概念計算來把握,這就是為什么二十世紀初葉德國出現自由法學運動,在美國出現了法學現實主義運動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社會越來越多元化,越來越流動化,我們很難按照一個形式的標準來要求它。反過來,把實質性的判斷放到程序之中,但是這種判斷不是任意的,也不是僅僅局限于某種價值取向,這就是新程序主義很重要的特征,新就新在這個地方。
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的轉型期,各種不同的利益訴求和多元化的價值觀并存,在此種背景下,程序對我們尤其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如何重建共識,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重新提出程序性共識的重要性。
俞可平:程序和價值不可分離
季衛東教授從現代、歷史、中國與世界、法學與哲學很多的維度和視點分析了程序和價值的關系,進而提出了他的新程序主義理念,通過新程序主義達到我們的共識。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理解程序和價值,以及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
我的看法是,程序和價值都是人類重要的制度,它們是不可分離、不可或缺的。對于任何重要的制度和實踐活動,事實上都會涉及到哲學上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國家,做任何事都離不開這兩種理性。價值理性就是目標、理想、理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常常是先驗的。而程序則是手段、是工具、常常是經驗的。今天這個論壇上,對兩者的區別季教授講得非常清楚。但是,這兩個理性,作為人類兩種基本的理性,雖然有區別,但從根本上卻不可分。季教授整個演講特別強調的是要實現一種價值理性,首先要強調程序。如果光是目標很遠大、很高尚,如果不擇手段的話,最后會帶來災難,這一點已經有大量的事實證明。有些改革很好,目標非常好,大家都很認可,形成了共識,但是制度設計、程序設計不公平、不合理,結果往往事與愿違。比如選拔干部,最近一個很大的改變,就是更多的競爭上崗,民主推薦。這非常好,比過去好得多,大大地推進了民主。但如果程序不嚴密,就會流于形式,被少數人操控,結果就很不好,甚至成為假民主。
但從對民主的定義而言,程序和價值必須結合起來,不能分離。民主講的是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但同時要保護少數人的利益,所以民主是一個寬容的、制約權力的、離不開公民參與的制度。民主需要公民參與,民主需要協商和對話,所以說民主是一種協商政治。總的來說,在目前我國這種環境下,要實現我們的價值,程序確實更加重要,這是我從政治學角度給季教授演講的評論。
張維迎:程序正義優先的考量
季衛東教授講程序正義,認為程序正義應該放在優先的地位,主要是從價值沖突來講的。也就是說,其實人類最終的目的是追求實質性正義,但我們很難有一個真正的、所有人都接受的實質性正義,在這個意義上,程序正義才更重要。對他的觀點,我覺得立意很高,論證很嚴謹,從思想史、歷史和現實案例幾個維度討論,相當有說服力。
季衛東教授認為每個人對同樣的事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價值判斷,這是法學上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是我個人認為,法學上還有一個重要的判斷或者更重要的判斷,就是來自于執法者本身。我們在討論很多法律問題的時候,一般講執法者本身是中性的,是超脫的,在這個意義上判斷法律制度的建設。其實執法者也不是判斷者,他和普通人一樣也有兩方面的局限性:一是他也有私利,二是他也和普通人一樣知識是有限的,雖然他受到很多法律專業的訓練。因此,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討論為什么要把程序正義放在優先的地位。
程序正義是一種法律“傻瓜”化的裝置。
我這里所講的法律“傻瓜”化,借用的是大家都知道的傻瓜相機的例子。為什么要用傻瓜相機?相對傻瓜相機的照相設備是非常專業的工具,比如變焦、曝光等等,有很多技術上的要求。對于普通人來說,這樣的專業相機不僅很貴,而且很多技術都無法掌握。而傻瓜相機就不同了,雖然我們能力有限、知識有限,但我們可以掌握它,因為我們不可能比傻瓜相機還傻。就程序正義而言,我們可以將法律本身變得傻瓜化一些,就不用太多地依賴執法者個人的價值判斷。
比如,我們經常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實仔細想一下,什么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相信,研習法律的人也講不清楚這個問題。我舉一個例子,假如有一個高級干部犯了強奸罪,只是接受行政降級處罰,另有一個農民犯了強奸罪,坐牢三年,大家說這樣平等不平等?大家當然會說不平等,因為同樣一個案子,干部可以很自由而農民卻要坐三年牢。但我們再想一下,假如開車,可能今天限號違章罰100塊錢,如果這個人一個月收入幾千塊錢罰他100塊錢,另一個人一個月收入幾萬塊錢也罰他100塊錢,這樣平等嗎?大家可能說很平等。其實,這兩個問題是一樣的。進一步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失去的平等還是留下的平等?從失去的平等來說,像強奸案就能說明,一個高級干部如果降級降得很厲害,他的痛苦可能比一個農民坐三年牢還要大。而同樣的罰款對不同收入的人的痛苦是不一樣的,我們為什么要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身就可能不平等。
基于此,在法律制度的設計中需要考慮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適度分離的問題。
王晨光:程序應內置價值判斷
季衛東教授的報告從路徑問題入手,以程序正義為基礎,提出新程序主義的理論框架和實踐進路,并以此作為進一步推進社會法制建設、社會共和的主要路徑。這個立意是非常高的。
在這個意義上,季衛東教授能夠從國內和國際多元化格局的大背景出發,抓住了解決多元化價值沖突的必然途徑,也就是程序途徑的角度,在對理論和現實的翔實和準確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新的值得重視的思路和進路。從這個角度講,提出中國法制重構的“新程序主義”不僅具有理論上的創新,更具有實踐上的必要。
但是,對于程序的規定而言,我認為應該有一個內設的價值判斷在里面。從這個意義上講,程序的問題并不可能完全脫離價值。因此,程序本身不僅在最初設定的時候有一種內在的價值內設,同時在運行過程當中有價值的導向在起作用,而且還有很多社會效果的考量。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我們講新程序主義,更多的強調法制的程序主義的優先原則,這是沒有錯的,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程序內在的一些價值存在,程序運行過程當中也受價值導向的指引。
很抽象的理論可能很枯燥,我講一個親身經歷的事情。兩周前到美國參加會議,在入關的時候,我被耽誤四個半小時。為什么?因為違反入境程序規定。我有一個有效的入境簽證,有效期一年;我認為拿簽證直接就進去了。但是按照美國法律規定,還需要有一個移民部門發的表格,但是邀請單位沒有給我發表格;因此僅僅有簽證而沒有表格則手續不全,無法入境。警察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沒表格,就必須回去”。雖然是這么說,她讓我在那坐了半個小時后開始問我具體情況,什么目的,邀請人是誰,然后開始聯系。因為正好是星期天,她很難找到單位的人,最后居然通過校園警察把邀請我的人從家里找到了,但是耽誤了四個半小時。到此,我認為就可以進去了,但還是不行,還得重新填表格,完成程序要求。這個程序跟原來的程序是不一樣的,在程序運行當中我們會發現程序存在設定的目的和價值,同時程序的運行還有一個可操作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