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仁善近著《中國法律文明》(共34萬字)2018年4月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當年即被列入”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shù)外譯學術(shù)叢書項目”英文翻譯項目。2019年,入選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等機構(gòu)評選的“新中國70年百種譯介圖書推薦目錄”,為法學學科入選的僅有的兩本著作之一,也是法律史學領(lǐng)域唯一入選的著述。2019年,又被“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shù)外譯叢書基金項”意大利文翻譯項目。據(jù)悉,目前該書的韓語、烏爾都語等翻譯授權(quán)立項工作也在進行之中。相信該書的海外發(fā)行,有助于推動中國法律文明走向世界的腳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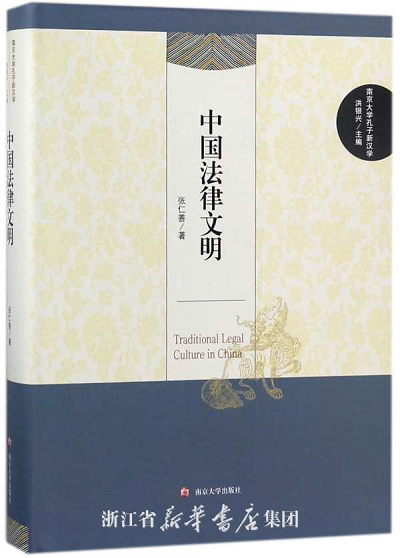
序 言
中國文明的起源,基于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與自然生態(tài),社會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及社會細胞,也有別于其他文明地域。在此基礎(chǔ)上,逐步出現(xiàn)了一系列與此相適應的社會準則。階級社會及國家確立之后,不少“準則”就上升為今天被稱之為“法律”的規(guī)則。中國法律文明與歷史文明相伴而生,獨樹一幟,巍然屹立于世界法律文明之林,其發(fā)展軌跡逶迤綿延,從未間斷。
本書由禮制文明、刑制文明、法理念文明、法體系文明、契約文明、調(diào)解文明以及司法文明等七章組成。中國法律文明天生具有其自身的民族特性,其發(fā)展走向與世界其他法律文明形態(tài)區(qū)別明顯。在歷史法學派看來,法律是一個國家民族精神的體現(xiàn),民族精神先于法律、語言、風俗等民族屬性,而與特定的民族實體共生、共存及共亡,法律要維護民族精神的現(xiàn)實狀態(tài),不能脫離特定民族的歷史,超越現(xiàn)實。發(fā)源于內(nèi)陸、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宗族結(jié)構(gòu)及中央集權(quán)等,均是中國文明產(chǎn)生的基礎(chǔ),只要自然、經(jīng)濟、社會及政治結(jié)構(gòu)沒有發(fā)生質(zhì)的變化,基于其上的規(guī)則體系也不會裂變。民族性越完整,法律越持久。
中國法律文明特征鮮明:法律淵源多元;法律形式多樣;彰顯德性、人本理念;維系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運行;與宗法制社會高度切合;完美體現(xiàn)一元化的政治意志;催生大一統(tǒng)局面的向心力,增強民族凝聚力;道德之治被內(nèi)化為規(guī)則之治;注重法律與天道、人倫的和諧;國家法與民間法的互動;司法中情、理、法的融合,理性與經(jīng)驗的統(tǒng)一;促進社會控制效力的最大化;在絕大數(shù)時間段,實現(xiàn)社會和諧穩(wěn)定。以中國法系為核心的中華法系曾經(jīng)引領(lǐng)東亞法律文明,塑造了東亞法圈,也為世界法律文明貢獻出智慧,世界法律文明的華章因此更加璀璨。
法律規(guī)則創(chuàng)制后,一邊供人們遵守,一邊用來修訂、健全。社會生活變了,時代更替了,法律也要隨之更改,保持與社會生活應有的適應度。與時代相適應的法律,才是好法律。特定時段的法律,在特定時段可能是優(yōu)良的,在另一個時段,也許成為社會發(fā)展的桎梏,變革在所難免。法國波塔利斯曾說過:“法律應當珍惜習俗,如果這些習俗不是陋習的話;只有在不革新是最糟糕的時候,才必須要變革”,習俗固然應當珍惜,但與時代發(fā)展不合節(jié)拍的陋習則應該廢除,需要革新。我國清末時論者也提出,“法律與世代相變遷,凡有宜古而不宜今之律當廢之而不援為法……律因時而制,時已迭更則因之者,亦與之遞變,蓋時勢為之也”,法律因時而制,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民族性本身也非一成不變,不會始終處于封閉狀態(tài),獨自演化,會不時受到其他文明的浸入。固有文明勢力的強弱、開閉程度不同,對于外來法律文明,本土法律文明會呈現(xiàn)拒絕、吸收或融合態(tài)勢,但因時而變,乃必然趨勢,只是有主動變革和被動變革之別。近代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文明在西方工業(yè)文明挑戰(zhàn)中落了下風,較之于近代西方法律文明,傳統(tǒng)法律的劣勢全然暴露,失去了與之角力的底氣。為了捍衛(wèi)民族主權(quán),應對社會變遷,法律也被拽上近代化之路。
只要民族特性沒有根本改觀,外來法律文明的影響大多體現(xiàn)于法律文明的表征。中國近代法律移植或繼受在法體系創(chuàng)制上成績卓著,在法律實踐的成效、民主法治精神的培養(yǎng)以及法治化社會的構(gòu)建等方面則不盡如人意。
民族的,未必是世界的。唯有民族中的精華,才有可能成為世界文明的元素;民族中的糟粕,不但是本民族發(fā)展的障礙,也不會為世界所接受。法律存在的合理與否,取決于與主客體行為發(fā)生時的社會實際相適應程度,是“那時”的法律,“那時”的事和人,而非后世評論者所處的“現(xiàn)時”的社會現(xiàn)實。傳統(tǒng)中國法律中,道德與法律界限模糊,身份等級差異明顯,過于看重熟人社會關(guān)系,行政、司法權(quán)限不清,義務本位重于權(quán)利本位,法律期待性不夠明確……諸如此類,均為傳統(tǒng)社會的產(chǎn)物,與現(xiàn)代法治社會要素鑿枘不合。
后人對待既往法律文明,既不能數(shù)典忘祖,全然否定祖制,亦不能妄自尊大,一切敝帚自珍;對祖輩創(chuàng)造的輝煌文明,當懷溫情和敬意;對時過境遷、日顯愚昧滯后之處,不時反省割棄。“傳統(tǒng)既是一宗包袱,也是一筆財富”,如果不對過去的法文化做一番深入的考察與評價,便無法理解中華法系是如何從傳統(tǒng)過渡到近現(xiàn)代,也就不能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借鑒與啟示,更不能為未來的法制改革獲得先機。唯有憑借對民族傳統(tǒng)精華的自信,對世界先進文明的海納,自我揚棄,不斷升華,保持與各法律文明之間的包容和互補,本土法律文明才能融入世界文明大潮,持久保持旺盛活力。
歲月疾逝,學無止境。如同法律一樣,個人也當與時并進,立足學術(shù)前沿,拓展研究視野,更新知識結(jié)構(gòu),吸收最新觀點,盡可能保持為學激情。古人早將“行路”與“讀書”視為一體,近年來,本人通過赴國外及臺灣等地訪學,從美國國會圖書館、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大英博物館、臺灣“中央研究院”圖書館及諸多大學圖書館查閱了大量資料,拍攝了不少圖片,多次參加國內(nèi)、國際學術(shù)會議,接觸國內(nèi)外同行,交流學術(shù)觀點,諸多活動,均有益于自己研究能力的提升。
本書的一些內(nèi)容、其中部分也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傳統(tǒng)司法中的理性與經(jīng)驗”的系列先期成果,曾發(fā)表于《法學家》、《華東政法大學學報》、《河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學報》、《法律文化研究》及臺灣《法制史研究》等學術(shù)刊物上,感謝上述刊物的諸位編輯。
“教學相長”一詞,在本書寫作過程中領(lǐng)悟愈深:書中的不少觀點,就直接來自多年來與相關(guān)專業(yè)的中外碩士生、博士生課堂討論或日常切磋中所受的啟發(fā)。從同學們那里,獲益良多,劉海波博士等學友,更是對參考資料的搜集等提供過一些直接幫助。享受教研過程,接觸青年才俊,葆有年輕心態(tài),對一名教師而言,足可自得其樂,慰藉寸心。
感謝南京大學孔子新漢學叢書的編委們選錄本書;感謝南京大學出版社對一再延遲交稿的寬諒;感謝人文圖書編輯主任施敏女士的耐心溝通指正;感謝責任編盧文婷女士付出的辛勞。
感謝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李懷印教授在英文目錄翻譯等方面提供的幫助,李教授也是作者老鄉(xiāng)及本科高一級同學。
2018年1月29日于南京金陵御沁園
作者簡介:

張仁善,江蘇東臺人,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南京大學法學院“司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律史學會執(zhí)行會長。主要從事中國法律史、法律社會史、司法傳統(tǒng)與司法近代化等領(lǐng)域的教學與研究。代表專著有:《中國法律文明》(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禮·法·社會——清代法律轉(zhuǎn)型與社會變遷》(商務印書館,2013)、《近代中國的主權(quán)、法權(quán)與社會》(法律出版社,2013)、《法律社會史的視野》(法律出版社,2007)、《司法腐敗與社會失控:1928~1949》(社科文獻出版社,2004)、《1949中國社會》(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當代中國黑幫》(江蘇人民,1998)等;編輯《王寵惠法學文集》(法律出版社,2008)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