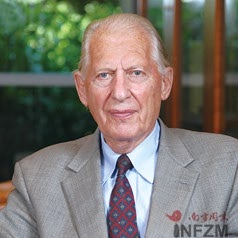上帝召喚他去了,從法律通往自己的懷抱。于我們而言,是一個巨大的遺憾,而對伯爾曼而言,則是精神意義上的一種完成。
上帝是一位公正的法官——引自伯爾曼《法律與革命》
●1918出生于美國康涅迪格州哈特佛市(Hartford)。
●1938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College)學士學位。
●1939倫敦經濟和政治學院研究生結業證書。
●1942耶魯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
●1942-1945供職美軍駐歐洲戰區,獲銅質星章。
●1947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1948-1989哈佛大學開設“世界法”和“比較法制史”課程
●1961-1962莫斯科大學教授美國法。
●1974出版《法律與宗教》。
●1983出版《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
●1985起任埃莫里大學(EmoryUniversity)教授。
●2003出版《法律與革命Ⅱ———新教改革對西方法律傳統的影響》。
2007年11月13日,鬼使神差地讀起了自己的一篇關于伯爾曼教授的舊文,心情莫名復雜,于是便寫下《轉載一下自己的心情》的文章。
詭異的是,第二天得知,伯爾曼在紐約溘然長逝,享年89歲。
在那篇博文中,我說:如果,如果過去的時光也能轉載,那就更好了。如今看來,這已成為一個永不能實現的愿景。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
對于中國的公眾來說,哈羅德·J·伯爾曼(HaroldJ·Berman)這個名字也許是頗為陌生的,但法律界的人,包括法學院里的莘莘學子,則深知其博大與光華。
伯爾曼是美國當代著名法學家,曾長年任哈佛大學法學教授,1985年榮退后仍獲聘美國埃莫里大學的最高榮譽教席——RobertW·Woodruff講座教授,曾以其代表著作《法律與革命》名震西方法學界,乃至享譽國際法學界,被認為是當代國際級的法學巨擘之一。
埃莫里大學在訃告中說:伯爾曼是“美國法學教育界學術最為淵博的學者之一,其法律思想敏銳的批判力和宗教影響力,使他在20世紀包括羅斯科·龐德、卡爾·盧埃林和朗·富勒在內的法學巨人的陣營中贏得了一席之地”。
伯爾曼的《法律與革命》和其上世紀70年代的《法律與宗教》都已在中國翻譯出版,并在這個國度的法律界產生了重大的反響。“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一語,更成為近年中國法律界中廣為援引和流傳的一句箴言。
筆者雖然沒有精研伯爾曼的學說,但作為中國的一介法律學人,也曾同樣為他的這一論斷所震撼,尤其是他所揭示的有關“法律與宗教之間的隱喻關系”,曾使本人陷入長久的苦思,直至去年領略到這位老人睿智而又仁慈的風采,那種苦思仍然縈繞于腦際。
而伯爾曼本身就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
他生長在一個猶太家庭,從小就讀希伯來圣經。他曾跟中國學人談起自己的信仰歷程。那是二戰即將爆發期間,他曾去歐洲訪問,并冒著可能被抓的危險,特意去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探望他熱戀的女友,在身份報表上填寫的是新教徒,并受到一個德國家庭的庇護,從而幸免劫難。
時值1939年夏天,大戰的陰霾已然密布了歐洲的天空,伯爾曼只好前往瑞士,但沒過幾天,因為想見女友,又折回德國。在輾轉的旅途中,他與逃亡的歐洲農民一道擠在火車上,感覺非常絕望,“以為以前學的對歷史的研究都沒有意義了,一切都要結束了”。
然而,就在有一天凌晨兩三點的時候,他隱約看到了耶穌在云端上的形象。從那個時候開始,他便成為一名基督教徒。
伯爾曼的個人信仰對其未來的學術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在他的代表作《法律與宗教》中,伯爾曼直接揭示了“法律與宗教的隱喻關系”。這本書是1971年在波士頓大學的講演集,伯爾曼曾說:這本書實際上也可以取名為《法律與宗教的互動》。這是一個薄薄的冊子,但其所產生的思想價值卻絕不“單薄”。
在這本書中,伯爾曼指出:在西方法律文化傳統的演進史中,法律與宗教的關系甚為密切,二者具有四個共通的要素,即儀式、傳統、權威和普遍性,其中,宗教賦予了法律以其精神、方向及其獲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
而伯爾曼憂慮的是:當代西方,法律與宗教的觀念均已陷入偏狹,以致割裂了傳統中法律與宗教的這種關系,尤其忽視了法律中應有的宗教因素,法律因而失去了神圣性而淪落為塵世中的一種工具。這便是西方法律文化傳統的巨大危機。
有鑒于此,伯爾曼指出: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也易于變為狂信,并吶喊“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
伯爾曼儼然是一個“二元神論”者,既信仰上帝,也信仰法律,他是看到了上帝與法律的一體性。
對于中國人而言,自然沒有類似伯爾曼個人的這種宗教情感可以“移情”到對法律的態度中去,連將法律視為有效的世俗工具,甚至作為統治者的“國之利器”,都幾乎只是“法家”式的哀愿。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之下,“法律必須被信仰”的論斷,不是被看成是癡人說夢,就是被注入某種悲情,從而其本身也就轉換為一種新的“隱喻”。
“《法律與革命》本身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
1983年,伯爾曼出版了傾注其45年心力完成的《法律與革命》,該書的副標題就是“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
在這一經典著作中,他與其他許多西方學者一樣,將法律理解為“活生生的人類經驗之一部分”,所不同的是,他重新詮釋了西方法律文化的傳統。
他發現西方法律傳統的演進史其實貫穿了幾場重大的革命,其中,11世紀末至12世紀初的教皇革命,曾統一了西方各地的教會權力,將其從皇帝、國王和封建領主的宰制中解放出來,形成了西方最初成型的法律制度──羅馬天主教會的教會法體系,并催發了與之分庭抗禮的各種世俗法律,諸如皇室法、封建法、城市法和商法。而在神權與世俗政治權力的劇烈對抗之中,法律得以上升為高于政治的統治地位。這便是西方法律文化傳統的濫觴;而自16世紀以降西方相繼爆發的多次革命,包括我們所熟知的英、法、美近代市民革命以及20世紀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起初都曾力圖與法律傳統決裂,但最終卻又不得不回歸這一傳統,并對這一傳統均有損益。
伯爾曼的這種深刻洞見,即便在西方學界也是頗為獨到的,無怪乎美國學者喬治·H·威廉斯說:“《法律與革命》本身就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美國政治科學評論》稱:此書“可能是我們這一時代最重要的法律著作。”《洛杉磯日報》也說:“每個法律家都應該研讀它……”
其實,伯爾曼的《法律與革命》還沒寫完,他生前已經在撰寫第三部。在2006年訪問中國的時候,他還自信地說:中國人同樣會對這一部感興趣的,希望自己能夠盡快寫完——“如果我活得足夠長的話,不過,這就要取決于上帝是否愿意看到這部書。”
但上帝似乎最終還是不愿意他為中國讀者遺留下這個部分。上帝召喚他去了,從法律通往自己的懷抱。于我們而言,是一個巨大的遺憾,而對伯爾曼而言,則是精神意義上的一種完成。
延伸了的“隱喻”
伯爾曼曾一直強調,“法律”是有兩種層次的,一個是“實在法”或“人定法”;另一個是包括“神定法”、“抽象法”意義上的自然法,即體現了自然正義的理念層面上的法。伯爾曼認為,對法律的信仰,是指并非對“實在法”的信仰,而是對“自然法”的信仰。
2006年5月14日,筆者直接聆聽了伯爾曼對這種“自然法”理論的演繹。那天,數百名嗷嗷待哺似的學子,填滿了浙江大學新校區大型國際演講廳里的所有坐位,一起仰望著講臺上的這位像法典一樣精致的老人。
伯爾曼講到:西方曾有法律實證主義、自然法學派以及歷史學派三大法律流派,時至當代,歷史學派已沒有多少影響力了,自然法學派也有所式微,只有法律實證主義居于上風,但他更傾向于自然法學派,因為自然法思想與人性更為契合。他舉出那個他曾多次說過的例子加以說明:你看一個五歲的小孩,從未學過法律,但他也會說:這個玩具是我的!這就說明他有物權的朦朧意識。他說:他打了我,所以我才打了他。這就說明他有侵權法乃至刑法的觀念。他說:你曾經答應過我的!這就表明了他有類似于合同法的意識。而當他說:這是爸爸允許做的,那么這就說明他已有憲法的觀念了。而所有這些觀念都是一個從未接觸過法律的五歲小孩自然而然擁有的觀念意識。
演講廳里不時地掀起陣陣笑浪,但筆者卻在座位上直接陷入了沉思。這個例子盡管相當輕松,但它畢竟出于一個擁有數十年學術生涯的睿智的老人之口,可能經過了皓首窮經的驗證、苦思冥想的推演。
記得去年那個晚上臨別之際,老人與我們感動地道謝,然后緩緩走下階梯,并迎來了留美出身的一位中國法律學人那更為動情、更為感人的西式擁抱……
而這一幕,恰恰可能象征性地構成了當今中國法律人與伯爾曼學說之間的另一種隱喻關系,猶如伯爾曼所揭示的西方文化傳統中法律與宗教之間的那種關系那樣,同樣留待我們予以無限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