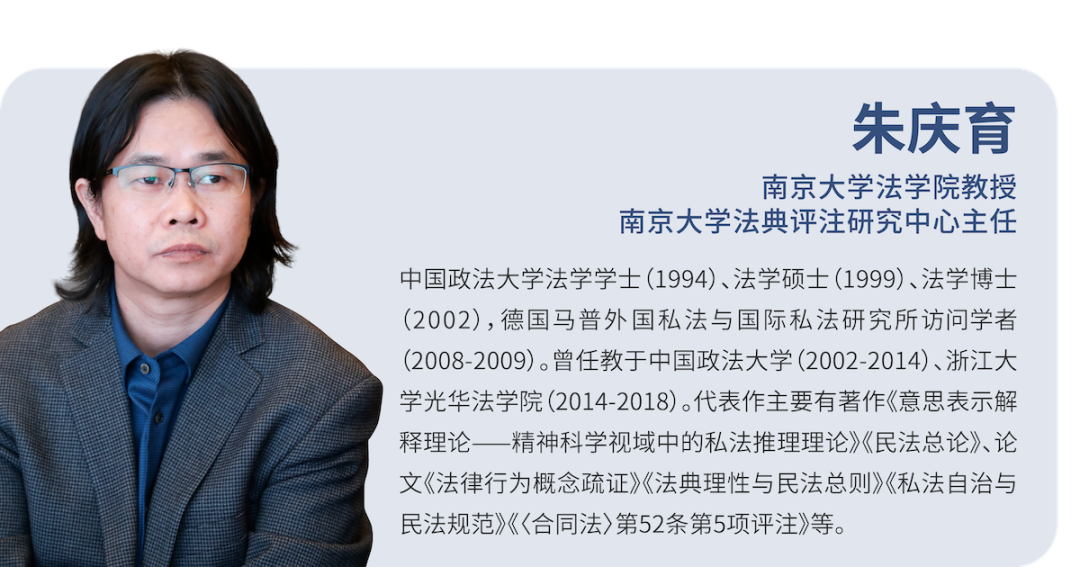
作者按:本文付梓之時,最高人民法院對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進行了部分修改,涉及本文討論的“金融機構的范疇”及“民間借貸逾期利率”等問題。下文已根據規范變動做出相應調整,尤其是段碼【13】、【27】及【33】的部分。特此說明。
摘要:《民法典》第680條是關于因借款合同而產生的利息債權及利率限制的規定,其主要目的在于限制利息暴利并尊重當事人的自發性。《民法典》在規范表達方面不再區分金融機構借款與民間借貸,但實際的二元構成并未改變。第680條作為不完全法條,主要通過金融監管部門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規定來實現利率規制的目的。與《合同法》不同,第680條區分了利息沒有約定與約定不明確的情形,同時“推定無償”的效果僅限于雙方均為自然人的借款合同。
關鍵詞:利率;金融機構借款;民間借貸;超額利息
目錄
一、規范目的與適用范圍【1-5】
(一)規范目的【1-2】
(二)適用范圍【3-5】
1、民法典生效前的“二元構成”【3】
2、民法典生效后的“隱蔽二元構成”【4-5】
二、“禁止高利放貸”【6-8】
1、“高利放貸”的意味【6】
2、宣示性規范【7-8】
三、借款利率規制【9-21】
1、“金融機構”的范疇【12-13】
2、金融機構借款的利率限制【14-21】
(二)民間借貸的利率規制【22-33】
1、借款期限內的利率【23-24】
2、逾期利息的利率【25-27】
3、復利的利率【28-20】
4、利率上限調整期間的規范適用【31-33】
(三)殘留的問題【34-41】
1、“利率”的意味【34-36】
2、金融機構借款利率的法律適用【37-39】
3、司法解釋與行政法規的關系【40-41】
(四)小結【42-45】
四、“利息沒有約定”的情形【46-58】
(一)規范屬性【47-49】
(二)要件: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50-53】
(三)效果:視為沒有利息【54-58】
1、“視為”的規范意味【54-56】
2、“沒有利息”的解釋路徑【57-58】
五、“利息約定不明確”的情形【59-72】
(一)要件:“對支付利息約定不明確”【59-62】
(二)效果:原則有償【63-69】
(三)效果:例外無償【70-72】
六、超額利息的抵充【73-77】
(一)“當然抵充”的裁判立場【74】
(二)“抵銷型抵充”與“當期型抵充”【75】
(三)法性質的判斷【76-77】
七、證明責任【78-87】
(一)貸款人的舉證【79-82】
(二)借款人的抗辯【83-87】
1、沒有約定利息【83-85】
2、利率過高【86-87】
一、規范目的與適用范圍
(一)規范目的
[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680條的規范目的在于對借款合同中的利息債權進行限制,防止利息暴利的產生。本條第1款通過限制利率來避免利息暴利的發生,第2、3款以利息債權的存在與否作為限制借款本金收益的手段。
[2]所謂利息債權,可以分為“作為基本權的利息債權”與“作為支分權的利息債權”兩種類型。“作為基本權的利息債權”與本金債權相互依存,以一定期間內全體利息產生為目的;而“作為支分權的利息債權” 以作為“作為基本權的利息債權”為基礎,以各期發生的具體利息的支付為目的,在移轉、消滅、訴訟時效起算等方面具有一定獨立性。[1]無論何種利息債權,其數額都是以本金與一定利率的乘積作為計算基準的,因此“利率”的數值對于利息債權的數額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二)適用范圍
[3]本條適用于所有類型的借款合同。
1、民法典生效前的“二元構成”
[4]在民法典生效之前,我國法上的借款合同長期區分為金融機構借款和非金融機構借款,在貸款主體方面是二元的。這樣的規范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國特定的金融管制模式。在我國,要從事經營性的借款活動,須以取得特定的“金融機構經營許可證”(以下簡稱“金融牌照”)為前提;但未取得金融牌照原則上并不影響借款合同效力。[2]因此,與市場構造相對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上的借款合同也是“二元”的。有觀點認為,《合同法》借款合同的二元構造是區分商事借款和民事借款的結果;[3]而后者一般被稱為“民間借貸”。實際上,所謂的民間借貸并不僅僅包括單純的民事行為,商人作為借貸主體的情形也極為普遍。
對應于上述的二元構造,借款合同的利率規制也是二元的。根據《合同法》第204條的規定,金融機構貸款的利率“應當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貸款利率的上下限確定”。而由于缺乏直接、明確的規范,實務中普遍以《合同法》第211條作為規制非金融機構的法人或非法人組織的借款合同利率的實體法依據。
2、民法典生效后的“隱蔽二元構成”
[5]雖然《民法典》沒有繼續采取類似《合同法》第204條的表達,而是以第680條“統一”規定了利率規制,消除了在規范表達層面的“二元構成”。但是,由于金融牌照的特許制繼續存在,民法典中的借款合同仍然是二元構成的,金融機構借款與非金融機構借款將繼續適用不同的規范。
二、“禁止高利放貸”
1、“高利放貸”的意味
[6]在《民法典》之前,民事法律規范中并沒有“高利放貸”的表達。在《民法典》整體草案2019年12月公布之前,《民法典》合同編的諸次審議稿中也沒有出現過該表達。之前,只有個別涉及刑事犯罪的司法文件使用了“高利放貸”的用語。[4] 由于“高”或“低”只是相對的概念,因此“高利放貸”的表達本身無法為“何為高利”提供標準。
另外,《民法典》并未采取過往司法文件中更為常見的“高利貸”的用語,[5]而是采取了“高利放貸”的表達。從語義上看,第680條第1款前段是基于貸款人的角度的,因此可以把第1款前段視為僅針對貸款人的行為。若貸款人高利出借貸款的行為系基于借款人高利借貸的引誘,則借款人的可責難性會強于貸款人。就此而言,“高利放貸”的表達為借款合同的類型化提供了線索。[6]
2、宣示性規范
[7]從效果層面來分析,本條第1款前段規定的“禁止高利放貸”是較為典型的不完全法條,[7]并未具體規定高利的標準以及高利放貸的法律效果;后兩者實際上是由第1款后段“轉介”至“國家有關規定”。就此而言,本條第1款是存在雙重轉介的構造,即前段的要件與效果依后段來確定,而后段的要件與效果則繼續轉介至其他規范。
[8]從立法論上來看,即使刪除本條第1款前段也不會影響后段的轉介,其他部門法對高利放貸行為的規制也在第1款后段的射程之內。因此,在解釋論上,應當將第1款前段視為單純的“宣示性條款”,僅僅是某種抽象立場的宣告。認為在立法中作出“禁止高利放貸”的表達就可以消滅高利貸的觀點,在邏輯和經驗上都是無法證明的。
三、借款利率規制
[9]《民法典》第680條第1款后段作為“不完全條款”,并未明確規定利率限制的具體內容,而是以“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規定將利率規制交由外在于《民法典》的“國家有關規定”;這樣的立場延續自《合同法》第211條第2款。
[10]學者指出,利率規制的規范目的就在于防止高利貸。[8]《民法典》第680條第1款后段為實現金融行政主管機關或司法機構制定的具體利率規制提供了“管道”,因此具有維護金融秩序的側面。[9]
[11]值得注意的是,第680條第1款所規定的“國家有關規定”的內涵較為豐富。《民法典》中多處出現了“國家有關……的規定”或類似的表達,但多數指向行政機構,[10]而第680條中的“國家有關的規定”的范疇則既包括金融主管、監管機關制定的金融政策,也包括司法機關所制定司法解釋,甚至還能被轉介至部分行政法規。對此,以下將具體說明。
(一)金融機構貸款的利率規制
1、“金融機構”的范疇
[12]根據《貸款通則》(中國人民銀行令(1996年2號))第21條的規定,構成第680條射程中的金融機構借款合同的,貸款人必須持有金融牌照且許可內容包括貸款業務。目前,業務內容包括貸款的持牌金融機構可以區分為銀行類金融機構和非銀行類金融機構。按照監管部門的規定,銀行類金融機構包括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社等能夠經營存款業務的機構,而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包括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托公司、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汽車金融公司、貨幣經紀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基金公司以及其他受金融監管當局監管的機構。[11]
[13]但是,在司法實務層面,“金融機構”的具體外延并不明確。然而,對于持牌金融機構的出借款項是否當然適用有關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的限制,現有的裁判實務并不統一。有法院以“地方法院公報案例”的形式認為消費金融公司是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其貸款利率不受民間借貸關于借款利率及逾期年利率的限制。[12]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也體現了上述立場。[13]但是,對于與消費金融公司在法律構造上較為類似的小額貸款公司(以下簡稱“小貸公司”),由于其是由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審批的,其發放的貸款被法院認為屬于民間借貸的范疇。然而,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負責人在2018年就《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轄的規定》(法釋〔2018〕14號)答記者問的內容中,小貸公司卻被明確當作金融機構之一。[14]對于金融機構的范疇,司法實務并沒有運用“穿透式思維”去重視“經濟實質”,而是困囿于多頭監管所造成的條框約束。直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適用范圍問題的批復》(法釋〔2020〕27號)2021年1月1日施行,由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監管的小貸公司、等七類地方金融組織才被排除在民間借貸的范疇之外。
2、金融機構借款的利率限制
(1)貸款利率
[14]根據《人民銀行法》的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是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法定機關。金融機構貸款的基準利率長期由中國人民銀行規定,而各商業銀行根據《商業銀行法》第38條,只能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貸款利率的上下限來確定貸款利率。
[15]1993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允許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在規定幅度內自由浮動。2003年,黨的第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進一步明確了“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方向。
[16]在具體利率政策方面,從2004年元旦起,中國人民銀行擴大了商業銀行自主定價權,企業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擴大到70%,下浮幅度保持10%不變。2004年10月起,金融機構(城鄉信用社除外)貸款利率不再設定上限。2013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取消了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的下限。需要說明的是,此后中國人民銀行仍然制定金融機構貸款的基準利率,因此金融借款市場上存在貸款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并存的“利率雙軌制”問題。
而在2019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邁出了“利率市場化”的重要一步,以具有一定市場化程度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oan Prime Rate;以下簡稱“LPR”)來替代貸款基準利率,每月20日發布。中國人民銀行意圖通過LPR新機制的發布來推動實際利率水平的下降,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多的助力。由此,“利率雙軌制”的問題不復存在。
[17]《民法典》的生效并沒有改變上述利率規制模式,金融機構貸款的利率仍然是以每月發布的LPR為基準。
(2)復利
[18]除了就原本的本金約定的利率之外,借款合同還存在“復利”的問題,即將利息計入本金重復計息。按照中國人民銀行《人民幣利率管理規定》(銀發[1999]77號)的規定,金融機構對于逾期貸款是可以“改按罰息利率計收復利”的。而現行的罰息利率,則由《中國人民銀行關于人民幣貸款利率有關問題的通知》(銀發[2003]251)號第3條予以規定,即罰息利率“在借款合同載明的貸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
[19]而對于金融機構收取復利,法院是承認相關約定的有效性的。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管理、處置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形成的資產的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01〕12號)第7條對此有明確的規定。同時,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復利的計算基數是借款期限內的應付利息,并不能就逾期利息計算復利。[15]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近來的案件中表明,收取復利的主體須具備金融機構的資格。該案中,受讓人受讓之債權系基于金融借款而產生的,債權包含了復利請求權。但法院認為受讓人并非金融機構,對于債權讓與時既存的復利和繼續產生復利都無權請求。 [16]
(3)循環信用利率
[20]信用卡業務是商業銀行金融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信用卡持卡人與商業銀行訂立了允許持卡人在特定周期內連續借款的基礎合同(信用卡使用協議)。在持卡人分期支付的情形中,商業銀行會因此收取循環信用利息。根據不同的消費情形,商業銀行收取的循環信用利息的年化利率在0%——20%之間。如中國農業銀行的循環信用年化利率最高可達16.04%,[17]中國建設銀行則可達18.25%。[18]需要注意的是,若以2020年8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LPR為基準,上述利率的最高值已經超過了LPR的四倍。
(4)委托貸款利率
[21]除了進行存貸款業務,金融機構還有大量的中間業務(通道業務),其中與貸款有關的主要是委托貸款。所謂委托貸款,是指金融機構作為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將委托人的資金出借給借款人,并監督使用、協助收回。根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商業銀行委托貸款管理辦法》的規定,受托人只是收取代理手續費,并不承擔信用風險。但從外觀上看,委托貸款的貸款人仍然是金融機構,由此就產生了如何確定利率標準的問題。
對此,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雖然委托貸款行為在金融監管的范圍之內,[19]但其實質上是民間借貸合同,應適用民間借貸的利率規制。[20]依此類推,金融機構通過中間業務形成非利息收入的,即便是以貸款合同為表現形式,其利息(代理手續費或服務費)約定不受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利率基準的限制。[21]
(二)民間借貸的利率規制
[22]由于借款合同“二元構造”的存在,不適用金融機構借款利率限制的情形,均會被視為“民間借貸”,從而適用民間借貸的利率規制。
1、借款期限內的利率
[23]據學者研究,利率規制的歷史在我國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新中國建立之后、《民法典》生效之前,司法機構的利率規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22]
最初,最高人民法院于1952年11月頒布了《關于城市借貸超過幾分為高利貸的解答》,原則上以“三分”作為城市借貸利率上限。
在1978年以后,隨著私人金融活動的日益活躍,是否需要設置全國統一的“利率紅線”成為重要的爭議問題。[23]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借貸案件意見》”),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四倍銀行利率”的“紅線”由此形成。
[24]而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民間借貸司法解釋》”)。該司法解釋規定了“三區間”的利率規制模式。即,年利率24%以下的利息債權處于“有效區”,年利率超過36%的利息債權處于“無效區”,而年利率在24%到36%之間的利息債權則處于“自然債務區”。但裁判實務似乎并不考慮“自然債務區”內當事人自動履行的可能性,會率直地以24%作為借款合同的利率上限。[24]
“三區間”的利率規制模式曾被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是《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主要亮點之一。[25]然而,施行未及三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修改〈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決定》于2020年8月18日公布,并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三區間”的模式戛然而止。根據修改后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以下簡稱“法釋〔2020〕6號”)第26條的規定,民間貸款的利率上限為“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而“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即為一年期LPR。以法釋〔2020〕6號施行當月的LPR為基準,2020年8月20日至2020年9月19日之間的民間借貸的最高利率從之前的年利率36%陡降為15.4%(2020年8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一年期LPR為3.85%)。
施行四月之后,法釋〔2020〕6號又被《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民事審判工作中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等二十七件民事類司法解釋的決定》(以下簡稱“法釋〔2020〕17號”)所進一步修改,但利率上限得以維持。
2、逾期利息的利率
[25]1991年的《借貸案件意見》以任意法規的形式將法定逾期利率規定為“可參照銀行同類貸款的利率”。
[26]2015年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29條則規定,約定的逾期利率不得高于年利率24%;當事人未約定借期內利率及逾期利率的,適用法定逾期利率6%;當事人僅約定借期內利率而未約定逾期利率的,貸款人可以按借期內利率主張逾期利息。對于按照借期內利率計算逾期利息,《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制定者認為這既是借款人逾期還款后的合同繼續履行,也可認定為損害賠償或違約金。[26]或多或少,前者會給人“事實合同理論”的印象。事實上,在借款人逾期的場合,違約責任之外,還有不當得利的可能;以“事實合同”說明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只是在說明上較為便利。[27]
[27]而法釋〔2020〕6號第29條第2款第1項則將約定逾期利率的上限規定為“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與借期內的利率上限保持一致。但是,法釋〔2020〕6號刪除了法定逾期利率,而是規定“既未約定借期內利率,也未約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張借款人自逾期還款之日起承擔逾期還款違約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邏輯上說,借款合同的利息為法定孳息,逾期利息則屬于“損害賠償”的范疇。將逾期的損害賠償作為利息來處理,是以“擬制”的手段擴大了利息的概念。[28]法釋〔2020〕6號將“逾期利息”回歸到違約損害賠償的范疇,在法性質上是正確的。然而,法釋〔2020〕6號第30條仍然將“逾期利息、違約金或者其他費用”一并作為“利息規制”的對象,這說明法釋〔2020〕6號第29條第2款第1項的修改實際上并未考慮到逾期利息的法性質與規范之間的邏輯整合。法釋〔2020〕17號第28條則進一步將上述規定中“違約責任”明確為“參照當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標準計算的利息”,實際上“倒退”至2015年司法解釋的立場,法釋〔2020〕6號在逾期利息法性質方面自覺或不自覺的“澄清”消弭無形。
3、復利的利率
[28]對于復利,198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25條否定了復利的合法性。之后1991年的《借貸案件意見》第7條雖然規定“出借人不得將利息計入本金謀取高利”,但該條后段仍然承認未超出利率紅線的復利的合法性。
[29]對于《借貸案件意見》第7條的規定,法院認為其“并未禁止雙方當事人協商一致將利息計入本金,只是說明禁止以計算復利方式謀取暴利”,從而認為“復利”本身并不為我國法所禁止。[29]這樣的立場在實務中是較為普遍的,與前述認為僅有金融機構才能收取復利的裁判形成鮮明的對比(段碼19)。對此,只能認為前述案件涉及金額較高,縮減利息有利于快速解決糾紛。
[30]學說上,代表性的學者認為《借貸案件意見》是否定自然人借款合同中的復利的合法性的;[30]但隨后也轉變了觀點,認為復利并未被法律所禁止。[31]另外,還有認為單獨的復利規制沒有必要的主張。[32]
4、利率上限調整期間的規范適用
[31]雖然市場對于最高人民法院降低民間借貸利率上限有一定的預期,相關征求工作在2019年底就已經進行,但由于法釋〔2020〕6號幾乎是頒布即施行,如何處理之前訂立的民間借貸(存量民間借貸)就成為問題。
(1)法釋〔2020〕6號的規定
[32]法釋〔2020〕6號第32條規定,法院新受理的一審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按照修改后的司法解釋處理,而“借貸行為發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參照原告起訴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確定受保護的利率上限”。從字面上看,“可”與“參照”本身都不具有強制意味,下級法院由此可以任意選擇裁判依據。從近來的實務狀況來看,有法院按原告起訴時LPR的4倍來計算借款利息;[33]也有法院以2020年8月20日為界限,之前的利息以本金為基準、按年利率24%計算,之后的利息以當月LPR的四倍即15.4%來計算。[34]還有法院在判決中認為,對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受理的案件,借款利息應當按照年利率24%計算。[35]由此,法釋〔2020〕6號第32條為債務人提供了采取機會主義行動的契機,即選擇LPR數值較低的某月就存量民間借貸提起訴訟,這樣可以盡可能降低利息總額。
(2)法釋〔2020〕17號的規定
[33]面對混雜的實務狀況,法釋〔2020〕17號第31條就存量民間借貸采取了“二階段”的利息計算方式,即以2020年8月20日為界,之前的利率以當時的司法解釋計算,之后的利率適用法釋〔2020〕17號的規定。
(三)殘留的問題
1、“利率”的意味
[34]在借款合同中,利息是根據利率來算定的。利率一方面是決定本金與利息比例關系的基準,另一方面在理論上也能劃定利息的具體范圍。[36]但是,無論是《民法典》第680條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都沒有特別說明“利率”的意味。司法解釋所規定的利率是“年利率”,是以利息總額除以實際本金總額所得結果,按照借款期限測算年度利率(利息÷本金÷借款天數×365)。因此,現行法中的利率應被界定為“年化利率”。
[35]然而,年化利率未必能反映真實的借款利率水平。在“息隨本清”的場合,利息與本金的比例是固定的。但在本金與利息按照一定周期還款的場合,則利率是處于變動之中的。無論采取等額本金還是等額本息的還款方式,由于利息與本金在還款周期內處于變動狀況,實際利率通常都會高于名義利率。如果說從利率上限從“年利率36%”到“LPR的四倍”是為了降低實際利率水平,那么年化利率的表達是否足以達成上述目標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
[36]更為重要的是,對于某些短期貸款或者超短期貸款而言,若將利率年化計算,則完全會背離市場規律;較為典型的狀況是“過橋借款”。在個案中,貸款人向借款人提供過橋資金借款,合同約定金額1500萬元,借期8天,提供借款時借款人向貸款人一次性支付前4天利息18萬元(“砍頭息”),之后按每天千分之三計。[37]若以該約定為依據,則該借款的實際年化利率為55.4%(1500×0.003×4÷(1500-18)÷8×365)。但該合同的實際利息為18萬元(1500×0.003×4),占本金總額的1.21%,實際占比并不顯著。若以當時的年化利率上限24%來限定借期利息的話,則貸款人能請求的借期利息總額僅為7.7957萬元((1500-18)×0.24÷365×8)。在短期內急需大量資金的情況,按照市場供求關系來確定具體利息數額并無不當;若一味以年化利率為指標,則顯然會抑制貸款人的出借動機,從而壓縮市場貨幣供應,與降低市場實際利率的初衷背道而馳。
可見,以“年化利率”為基準的利率限制模式僅適合于中長期借款,應限縮司法解釋的規定,在短期、超短期借款的場合根據市場供求來確定合理的利率水平。
2、金融機構借款利率的法律適用
[37]于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金融機構貸款是否應當適用民間借貸的利率限制。雖然《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1條明確將“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規定為非適用主體,但即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對該問題的立場也是分裂的。在有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承認“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借貸的利息、復利、罰息、違約金、其他費用等總計融資成本的最高限制并無明確的法律規定”的同時,認為本著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宗旨,金融機構不應追求過高“剩余價值”,從而“金融借貸利率不應高于民間借貸的利率……”。[38]2017年8月印發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第2條可謂該立場的抽象表達。最高人民法院的近來判決也延續了上述立場,仍然將民間借貸的利率上限作為金融機構借款利息范圍的界限。[39]即便是銀行發放的貸款,法院也判決“罰息、復利之和不得超過以貸款本金人民幣3億元為基數按年利率24%計算的范疇”。[40]
[38]但是,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紀要》”)卻指出:“區別對待金融借貸與民間借貸,并適用不同規則與利率標準”。于是,在金融機構借款利率的規則適用方面,“言行不一”成為當下實務立場的特征。
[39]金融機構發放的消費金融貸款和小額貸款則通常借款期限短、借款額度低,在結構上與中長期貸款形成互補,同時也是金融機構重要的利潤來源。例如,螞蟻金服旗下的“花唄”是小貸公司,其出借的款項一般是以日利率基準計算利息的,通常的日利率在0.05%左右,[41]折算成年利率為18.25%,低于24%。但若以2020年8月20日LPR的四倍為基準,則顯然超過了法定限度。目前民間借貸的利率上限近乎“腰斬”,若仍然堅持將該限制適用于金融機構借款,則對金融業的整體影響不容小覷。近來據說出現了對銀行存量貸款按照LPR四倍計息的判決,[42]這對于消費金融和小額貸款不啻于是極為沉重的打擊。
3、司法解釋與行政法規的關系
[40]國務院于2020年7月1日通過了《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該條例針對的是機關、事業單位和大型企業因采購貨物、工程、服務而產生的應支付中小企業的款項,意在解決中小企業被拖欠相關款項的問題。從規范的事實對象來看,中小企業的應收賬款并非其對機關、事業單位和大型企業的借款,但邏輯上無法完全排除應收賬款轉換為借款的可能。若某一大型企業與提供貨物的下游中小企業就買賣欠款達成還款協議,以借款合同的方式達成展期,則中小企業的應收賬款會轉換為借款。而《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第15條規定:“機關、事業單位和大型企業遲延支付中小企業款項的,應當支付逾期利息。雙方對逾期利息的利率有約定的,約定利率不得低于合同訂立時1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未作約定的,按照每日利率萬分之五支付逾期利息”。“每日利率萬分之五”年化后的利率為18.25%,高于2020年8月20日LPR的四倍。此時,大型企業等能否主張按照《民間借貸司法解釋》或法釋〔2020〕17號的規定來劃定利率上限?
[41]行政法規與司法解釋競合的情形在實務中并不罕見。在有關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規定存在差異的情況下,法院會按照司法解釋而不是行政法規的立場來裁判相關糾紛。[43]但考慮到上述行政法規的趣旨,與中小企業欠款有關的法律爭議應當會被置于該行政法規的射程之內。或者也可以將上述條例的對象嚴格限定為基于買賣、勞務提供、工程建設等合同產生的債務,排除借款合同的情形,從而避免沖突的產生。但是,在極為接近的時間內頒布規范對象方面可能會有重疊的不同法律文件,該現象本身就是應該要避免的。
(四)小結
[42]實際上,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有關借款合同的討論仍然主要聚焦于“主體規制”或者“類型化”;而且,維持借款合同的“二元構成”也成為當下的共識。[44]在利率規制模式方面,《民法典》仍然沿襲了既有的立場,本身的條款并沒有提供直接的依據。由于第680條的射程覆蓋了金融機構借款與民間借貸,因此該條所呈現的利率規制內容在《合同法》第211條的基礎上實現了“倍增”。
[43]而在具體規范模式方面,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為主導的控制方式也極具特色。雖然金融機構貸款是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利率為基準,但法院通過裁判實務已經將金融機構貸款的相當部分納入了民間借貸的范疇。但這樣的傾向無論是在《民法典》還是司法解釋層面都難以獲得直接、明確的正當性。實際上,由法院來主導高利率的標準,從中長期看是缺乏“可持續性”的。中國人民銀行改革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之后,“利率市場化”改革又推進了一大步。可以想見,在不久的未來,體現即時貨幣供求關系的“市場利率”會取代“央行基準利率”,此時的高利率標準將主要是由市場決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否有能力“及時”、“準確”地對貨幣市場行情做出判斷,可能是需要質疑的;有學者就認為,最高人民法院的做法實際上會破壞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相關努力。[45]如果法院將來是以市場利率作為裁判的基準,那么只要結合個案情況考慮約定利率與市場利率的背離程度就足夠了。與央行基準利率“掛鉤”的利率上限除了能夠減輕法官在個案中的說理責任,恐怕并無其他明顯的增益。[46]
[44]在百余天內,法釋〔2020〕6號、法釋〔2020〕17號對《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連續修改可謂司法解釋歷史上“空前”的狀況,是否存在兩者合并為一次修訂、以避免對實務與市場的沖擊的可能?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于為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法發〔2020〕25號)第13條將“抓緊修改完善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司法解釋,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作為“促進金融和民間資本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具體手段。可見,至少法釋〔2020〕6號的出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策的考慮,并未重點追求法的邏輯性與體系性,也就需要法釋〔2020〕17號來打上“補丁”。如此頻繁的規范調整,一方面反映了我國金融市場的活躍程度,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規范模式的不成熟。
[45]從根本上說,高利貸是因市場供求關系而形成的,與金融市場的管制模式也密切相關。我國金融改革的目標是市場化,其法律表達就應當是“尊重市場主體的意思”。無論是現行法還是司法解釋可能都傾向于客觀的“等價交換”,并未重視合同自由。如果立法論層面的討論到此為止,解釋論的努力方向就值得繼續的檢討。
四、“利息沒有約定”的情形
[46]與《合同法》第211條第1款不同,《民法典》第680條區分了“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與“約定不明確”的情形,分別賦予不同的法律效果;其中,第680條第2款規定了無償借款的情形。由于金融機構借款都是基于其內部“自上而下”制定的格式合同,合規貸款不存在“沒有約定利息”的可能,因此本款主要適用于民間借貸。
(一)規范屬性
[47]第680條第2款規定的要件為:借款合同當事人“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其表達與《合同法》第211條第1款前段的內容是一致的,因此有關《合同法》第211條相關規定的討論也適用于民法典第680條第2款。
[48]學說上,關于上述規定的規范屬性,存在著不同的理解。一種觀點認為,上述規定屬于“意思推定規則”,[47]是意思表示的解釋規范,用以確定當事人未明確表達的合同內容。學者認為,該推定規則可以緩解訴訟當事人在舉證方面的困難。[48]同時,該規則對應的是“不可推翻的事實推定”,性質上屬于擬制性規定。[49]該立場可以被概況為“補充解釋說”。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上述規定與意思表示解釋無關。《合同法》制定不久,就有學者指出,《合同法》第211條第1款的適用以“經補充解釋仍無結果”為前提;[50]就此而言,第211條第1款的適用應當是補充解釋之后的作業——這可以被稱為“補充解釋優先說”。
還有觀點認為211條第1款并非是意思推定規則,其目的并非是擬制當事人的合意,而是在效果層面否定利息支付請求權。[51]同時,上述規定是“一個典型的有制度成分的任意規范”,能夠排除補充解釋的適用。[52]這樣的立場可以被稱為“任意法規適用說”。
[49]關于“補充解釋”與“任意法規適用”的關系,當下多數學說的觀點是認為應當貫徹“任意法規優先于補充解釋”的立場,[53]少數學說則認為“補充解釋優先”。[54]實際上,“任意法規優先”的觀點具有強烈的比較法背景,或許只有在類似德國法的語境中才能成立。[55]《民法典》的“合同編”有數處使用了“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表達,絕大多數的場合都須先經補充解釋方能適用任意法規,且幾乎都產生積極效果(如《民法典》第510條)。《民法典》第680條第2款則并未強調補充解釋,并且直接產生了消極效果——這似乎是立法者有意要排除“補充解釋”。但是,是否存在“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情形,仍然是合同解釋的結果。如果將補充解釋歸入合同解釋的范疇,[56]則事實上是無法排除補充解釋的優先地位的。因此,在本文的立場上,《民法典》第680條第2款仍然是較為典型的任意法規,根據“意思自治”的原則,應以意思表示解釋的結果為其適用前提。
(二)要件: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
[50]若借款人出具的借條中并未約定利息,當事人對此事實并無爭議,則法院會認定借款合同沒有約定利息,從而駁回貸款人的利息支付請求權。[57]對于借款合同是否存在“利息約定”,裁判實務也并不限于書面合同,而是重視探究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最高人民法院在個案中不僅認定借據中沒有利息約定,還基于案件的其他證據以及當事人借款交易的歷史認為當事人之間并沒有約定利息。[58]
[51]而在一些并沒有明文利息約定的案件中,法院則認為借款人關于借款合同“沒有約定利息”的主張不成立。例如,有判決認定,即便雙方當事人雖然對于借款的利息沒有明確的書面約定,“但從雙方當事人對于合同的履行情況看,借款為有息借款”。[59]而若借款人收到借款后出具的借據上載明的金額高于實際收款金額,雖然合同中并沒有利息的約定,法院仍會推定差額部分構成利息。[60]類似的,在借款合同未約定利息的場合,若借款人收到借款后退還部分給出借人,法院會因此認定這部分金錢就是借款合同的利息。[61]
[52]需要說明的是,第680條第2款規定的“沒有約定”的對象是“利息”,并非“利率”。《合同法》生效之前,1991年的《借貸案件意見》第8條針對“利率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情形,規定“借貸雙方對有無約定利率發生爭議,又不能證明的,可參照銀行同類貸款利率計息。借貸雙方對約定的利率發生爭議,又不能證明的,可參照本意見第6條規定計息。”
由于上述司法解釋的存在,在裁判實務中,有下級法院在當事人未約定利息的情形中,依據《借貸案件意見》第8條,判決借款人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支付利息。對此,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因借貸雙方沒有約定利息,……(保證人)不應承擔利息的上訴主張,具有事實及法律依據,本院予以支持”。[62]
[53]在有的案例中,借款合同并無明文利息約定,法院會認為“借款系用于房地產開發的事實,原審對蔡中悅要求利息的主張按照各筆款項實際支付的時間,參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予以支持是適當的。”[63]此時,法院是通過借款人的“經濟目的”補充解釋了當事人的意思,實際上會將“職業放貸人”等排除在第680條第2款以及法釋〔2020〕6號第25條所規定的“自然人”范圍之外。[64]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第680條第2款的適用是“劣后”于“補充解釋”的。但是,同樣是沒有明文利息約定的案件,裁判結果的差異說明了法院在運用補充解釋方面的“積極性”可能會影響法的安定性。
關于上述案件,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法院認為借款人不支付利息是“有違公平原則”的。這大致可以被理解為有關金錢給付中利息請求的“當然返還說”。[65]所謂“當然返還說”,是認為通常金錢都會產生利息,受益人應當返還受益及其利息,其主觀樣態則在所不問。[66]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裁判例也支持了上述立場。[67]
(三)效果:視為沒有利息
1、“視為”的規范意味
[54]第680條第2款在法律效果方面使用了“視為”的表達。正如學者所指出的,“視為”是我國法律規范中較為常見的用語。[68]對于“視為”的法性質,有認為其屬于“一種不容當事人反駁的法律擬制”;[69]也有觀點認為,現行法中的“視為”的法性質是多元的,可能是“推定”,有可能為“擬制”,或者可能是“注意規范”。[70]
上述觀點多是基于“視為”與“推定”、“擬制”在抽象的法學意味方面的異同而展開的。但是,所謂的“視為”恐怕并非嚴格的法學“術語”,具體立法者在條款形成之時是否充分考慮了“視為”的內涵也可能存在疑問。同時,“推定”與“擬制”本身就是多義的,需要在具體場合中予以說明。[71]因此,法律規范的“表達”只是解釋的出發點之一,可能并不具有“終局”的意味。對于“視為”的意味,仍然需要從具體規范的性質與目的中尋找線索。[72]
[55]按照本文的立場,第680條第2款的適用是在補充解釋之后的(段碼49)。此時,已經不存在推定“當事人意思”的必要,法院只須以第680條第2款為依據,直接導出“沒有利息”的法律效果。而若當事人證明相反事實,則在補充解釋階段就可以排除該條款的適用。就此而言,第680條第2款中的“視為”并非表達“事實推定”,而是某種擬制。但是,該擬制“能否反證”并非問題所在,事實證明是前置于該條款適用的。
[56]之所以擬制“沒有利息”的狀態,是由于沒有約定利息的借款合同被認為是“維護當事人之間的信任,弘揚友好互助精神”的;[73]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場也是如此。[74]
也可以認為,立法者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借款合同,即未附利息的借款與附利息的借款。歷史上,前者被認為是基于“恩惠的合意”(conventio benefica),后者則是基于“負擔的合意”(conventio onerosa)。[75]而當下的理論則更多地以“有償、無償二元論”來予以說明。[76]
2、“沒有利息”的解釋路徑
[57]第680條第2款在效果方面所使用的表達是“沒有利息”。從解釋論的角度來看,“沒有利息”有兩種理解進路。其一是將其理解為貸款人處并無利息請求權;其二是理解為貸款人有利息請求權,但借款人有權提出不支付利息的抗辯。需要注意的是,法釋〔2020〕6號第25條并未使用“視為沒有利息”的表達,而是規定“出借人主張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不予支持”的表述在法釋〔2020〕6號中被多次使用,有的可以被解釋為實體請求權不存在(如第22條),有的情形中則是存在實體請求權的(如第28條)。因此,司法解釋并未明確現行法的解釋進路。而《民法典》第680條第2款則改變了《合同法》以來的表達,將“沒有約定利息”的法律效果規定為“視為沒有利息”。這樣的否定性表達可以直接理解為貸款人處并未發生利息請求權。
[58]當然,上述理解是遵循文義的解釋,在《民法典》體系中或許會存在不同的理解。在本文的立場上,會傾向于“抗辯權發生”的立場。第680條第2款以及法釋〔2020〕6號第25條第1款、第2款前段都是“保護借款人”的規定。只要與公序良俗無涉,借款人當然可以放棄保護而支付利息。而且,從尊重當事人自發性的規范目的出發,原則上也無須訴諸意思表示以外的他律因素。因此,第680條第2款以及法釋〔2020〕6號第25條第1款、第2款,都是典型的“任意性規定”,并不帶有“強行法規”的色彩。借款人自身才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斷者,自然要尊重其意思。相對于“權利不發生”的立場,“抗辯權發生”能夠賦予借款人更大的自治空間,這實際上是提高了借款人的受保護程度。這樣解釋借用了“時效期間屆滿”所產生的抗辯權的法律構造,因此在借款人并不主張抗辯的場合,法院不得依職權來援引第680條第2款。
五、“利息約定不明確”的情形
(一)要件:“對支付利息約定不明確”
[59]第680條第3款的規定針對當事人對利息“約定不明確”的情形。《合同法》第211條曾對“沒有約定利息”和“利息約定不明”的情形賦予同樣的法律效果。學者指出,“約定不明確”意味著當事人之間存在有關利息的約定,只是在計算方面(利率)約定不明確,與“沒有約定”并非是同一情形。[77]從邏輯上說,“沒有約定”與“約定不明確”存在事實前提的差異,即前者“無約定”,后者“有約定”。在事實認定方面,“約定不明確”只可能被認定為當事人之間“有約定”或者“無約定”,并無第三種可能。因此,否定說的觀點是較為有力的。《民法典》草案合同編(二審稿)在“自然人借款”方面仍然延續了《合同法》的立場。但《民法典》最終區分了兩者。
[60]同時,“約定不明確”的情形被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是借款合同存在“漏洞”;[78]其他合同中的“約定不明確”也是如此。[79]學說上,這樣的觀點也能獲得支持——“當事人約定不明確”被認為“合同漏洞”的表現之一。[80]但是,所謂的“合同漏洞”并非是任意條款的缺少,而只能是實現合同目的的必要條款的缺失。[81]如果僅僅從客觀角度來理解“合同目的”,則利息條款顯然并非借款合同的必要條款——借款合同本身可以是有償的,也可以是無償的。如果合同漏洞并不存在,自然也就不需要進行補充解釋的作業。此時,要認定合同漏洞的存在,就需要“主觀”地去理解合同目的。在擴張“合同目的”內涵的同時,如何避免解釋的恣意將就會成為困難的課題。[82]
[61]事實上,裁判實務幾乎是將“利息約定不明確”等同于“利率約定不明確”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釋“利息約定不明”時,將借款合同雙方當事人都承認存在利息約定、但就利率發生爭議的情形作為例子;而解釋的主要內容則在于強調如何確定借款合同的“利率”。[83]
[62]從規范史的角度來看,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頒布的《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民通意見》”)第124條規定:“借款雙方因利率發生爭議,如果約定不明,又不能證明的,可以比照銀行同類貸款利率計息”。1991年的《借貸案件意見》第8條規定“借貸雙方對有無約定的利率發生爭議,又不能證明的,可參照銀行同類貸款利率計息。……” 其中,利率“不能證明”是指“雙方經過舉證質證,人民法院認為該事實仍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84]上述《合同法》制定之前的司法解釋都是針對“利率不明”的情形作出規定,而非“利息不明”。
因此,在解釋論上,應將第680條第3款所規定的利息“約定不明確”解釋為“利率約定不明確”。此時,才存在通過狹義合同解釋、補充解釋或者任意法規適用來補充當事人意思的可能。
(二)效果:原則有償
[63]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借款合同的“無償”實際上是羅馬法的歷史殘留,而當下“無償”利用他人金錢的情形可能早已不是借貸的典型情形。[85]由此,根據第680條第3款的規定,即便利息約定不明確,原則上借款合同仍然是有償的,只是需要通過“當地或者當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習慣、市場利率等因素”來確定具體的利率標準。
[64]與“沒有約定利息”的情形不同,在“利息約定不明確”的場合,重要的作業在于對“利息約定”做出合理的解釋。由于此時存在當事人之間的約定,具有明確的解釋對象,因此上述作業屬于合同解釋的范疇。當然,若當事人對此達成補充協議,則當事人的意思優先。
問題在于,此時解釋的目標是當事人的真意還是合同內容的規范意味?根據《民法典》第142條第1款的規定,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并不以追求真意為目標,《民法典》第510條規定的合同解釋基準也是以客觀為主,同樣的判斷也適用于第680條第3款。[86]
[65]在裁判實務中,若借款人僅僅在收據寫明“借期一年,按中國人民銀行利率計算”,法院認為該利率約定并不明確。[87]另外,若當事人在《借款擔保合同》中約定“借款利率另商,借款人出具承諾書”,則法院會認為借貸雙方并未對利率進行明確的約定,此時“通常的理解和民間借貸的交易習慣”等“客觀基準”會被當作補充解釋的重要依據。[88]
[66]重視客觀基準對利率進行補充解釋在2015年《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中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體現。根據法釋〔2020〕6號第25條第2款,借款合同利率約定不明的場合,補充解釋的基準為“結合民間借貸合同的內容,并根據當地或者當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習慣、市場利率等因素”。很顯然,“交易方式、交易習慣、市場利率等因素”均為客觀解釋基準,“民間借貸合同的內容”則存在主觀與客觀兩種理解路徑。
[67]《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發布之后,“合同的履行情況及市場上普遍資金使用成本”等客觀因素會被作為法院確定特定利率的正當化依據。[89]另外,法釋〔2020〕6號第25條中并未出現的“當事人身份”也可能對法院認定具體利率產生影響。[90]以上裁判例說明,法院有著區分民事交易與商事交易的“潛意識”,以及對借款合同當事人之間的“實質公平”的較為強烈的追求——這或許也是對上述“當然返還說”的進一步說明。
關于“當事人身份”對借款合同的影響,可能還有另一種解釋路徑。近來,“套路貸”成為了重要的社會問題,從最高人民法院至下級法院,都出臺了相關的政策或規定;[91]其中,所謂“職業放貸人”也成為了規制的重點之一。[92]一旦貸款人被認定為“職業放貸人”,當下的司法裁判多會嚴格審查貸款人主張與證據之間的關聯、是否涉嫌犯罪等,但對合同的實體法審查似乎與其他借款合同并無實質差異。[93]事實上,在2019年下半年之前,不管是貸款人自認為“職業放貸人”[94]還是法院認定其為“職業放貸人”,[95]借款合同的效力并不會因此而受到影響。與普通的自然人貸款人相比,“職業放貸人”身份的不利之處可能只是體現在稅收方面。例如,有地方規定,“對涉及職業放貸人名錄人員為申請執行人的民間借貸案件,本金與利息已經執行到位的,人民法院執行部門應當向稅務機關通報,由稅務機關依法征稅”。[96]然而,上述規定并未說明稅務機關將以何稅種以及稅率對職業放貸人的本息收入進行課稅。
當然,當事人的主觀因素并非全然被拋棄。若當事人未明確約定利率,而債務人自行承認的債務總額超過了本金,法院認為超額部分構成利息。此時,法院進行補充解釋的基準就在于“當事人的意思”。[97]
[68]但是,在2019年11月《紀要》之前,下級法院出現了因貸款人為“職業放貸人或其關聯關系人”而認定借款合同無效的情形。[98]借款合同被無效之后,本金返還之外,法院認為借款人應按年利率6%向貸款人支付“資金占用費”。[99] 而這樣的立場得到了《紀要》的肯定;《紀要》第53條規定:“未依法取得放貸資格的以民間借貸為業的法人,以及以民間借貸為業的非法人組織或者自然人從事的民間借貸行為,應當依法認定無效”。
[69]上述短期內的、集中的規范變動,除了“法的安定性”方面的疑慮,對“身份”的重視是否回到了過去“借款主體管制”的規制進路,以及私法裁判在實現特定“政策目的”的過程中的角色都值得進一步的討論。[100]有學者就指出,《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25條的存在將大大降低裁判結果的可預測性。[101]
(三)效果:例外無償
[70]例外的,在自然人借款的場合,若當事人對利息約定不明確的,會被“視為沒有利息”。由此,無論是“利息沒有約定”還是“利息約定不明確”,自然人借款都不會生成利息債權。如前所述,“利息沒有約定”還是“利息約定不明確”的事實對象是不一致的,邏輯上無法做類似的評價(段碼59)。但《民法典》延續了《合同法》的立場,表明了立法者對自然人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的“偏愛”。
[71]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狀況,是因為自《合同法》以來,關于自然人之間的借款,規范的出發點主要基于“尊重善意的自發性”的考慮,認為“在實踐中往往是當事人出于互相信任或者善意幫助發生借貸關系,當時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為維護當事人之間的信任,弘揚友好互助精神”。[102]同時,對“金融秩序影響有限”可能也是立法者將自然人借款作為獨立類型的原因——“自然人之間借款的數額一般較小”也是上述立場的理由之一。[103]
另一種可能的解釋在于,立法者有意識地區分了民事借款和商事借款,從而對第680條第3款后段進行了“目的性限縮”,即將其中的“自然人”解釋為“非商人的自然人”。 [104]
[72]基于上述規范意旨,具有商事或經營特征的借款合同被排除出第680條第3款后段的射程。余下的問題便是:后段的適用是否以借款合同雙方均為自然人為要件?在《合同法》生效期間內,雖然第211條規定的也是“自然人之間的借款”,但司法裁判也并未受到“自然人”的文義限制。在自然人向法人出借款項、[105]借款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均為法人、[106]法人向自然人出借款項等情形,[107]法院都認為應當適用《合同法》第211條。這是由于《合同法》在規范表達上采取了明確的“二元構成”,導致法院不得不通過對“自然人之間”的擴張解釋來解決具有商事或經營特征的借款合同爭議。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借款合同的主體限制已經逐步成為歷史。[108]正如學者所指出的,“總體而言,歷史上借款交易中的借貸主體管制,當前已不復存在”。[109]因此,無須再從放松管制的視角對相關表達做出解釋,第680條第3款后段的“自然人之間”便意味著借款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均為“自然人”
六、超額利息的抵充
[73]與利息超過法定限制相關的另一個問題在于:借款人能否主張超額利息抵充借款本金?對此,現行法及司法解釋并未提供直接的答案。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20條規定了“清償抵充”的相關規制,但上述條款針對的事實對象是借款人的還款沒有明確的清償對象。而超額利息的抵充要考慮的是:借款人就某一筆借款產生的超額利息能否抵充該筆借款的本金,或者能否抵充同一當事人之間的其他借款的本金?就借款人的清償而言,超額利息是基于特定清償對象(特定利息債務)而產生的,即其清償對象是明確的。因此,司法解釋的上述規定并不能直接適用。
(一)“當然抵充”的裁判立場
[74]自最高人民法院以下,裁判實務是普遍承認超額利息抵充借款本金的。無論是民事案件,[110]還是商事案件,[111]在超額利息抵充本金方面法院是相當積極的。
值得注意的是,與一般的民事訴訟不同,似乎不需要借款人的請求或主張,法院就可以直接在借貸案件中“依職權”將超額利息抵充本金。最高人民法院曾在判決中表明,若已支付的利息超過法定限制,則“高額利差應沖抵本金”。[112]此時,借款人是否有此主張完全不在法院的考慮范疇之內。甚至,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在沒有借款人請求的情況下,貸款人認為“二審判決將超過利率上限的利息直接在本金中扣減”的做法“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等申請再審事由沒有事實與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113]對于這樣的立場,學者將其概況為“當然抵充”。[114]
(二)“抵銷型抵充”與“當期型抵充”
[75]而關于超額利息如何抵充剩余本金,法院通常會有兩種做法,可以分別稱為“抵銷型抵充”與“當期型抵充”。所謂“抵銷型抵充”,是指法院在借款到期后,以全部本金和合法利率為基準,計算出合法利息的總額,借款人已經支付的利息若超過該數額,其差額“一次性”地抵充剩余本金。自最高人民法院以下,這樣的例子較為普遍;有的裁判文書對此計算方法有較為詳細的說明。之所以這樣的抵充方式應當被稱為“抵銷型”,是因為法院以借款人的超額利息返還請求權來“抵銷或部分抵銷”出借人的本息請求權,從而實現“清算”方面的便利。
也有法院意識到,在存在支分權的利息債權的場合,借款人每一期支付的利息中就可能包括了超額利息,因此應當就每一期的超額利息來判斷抵充本金的情況。例如,有法院認為,“對于每一筆還款,應分別根據還款時產生的利息,按照先沖抵利息后沖抵本金原則予以抵扣。” 很顯然,這樣的抵充方式會使得每一期超額利息發生時,本金數額會有相應的縮減,更有利于保護借款人并限制高利貸。實際上,在《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出臺之前,這樣的作法在裁判實務中也并不罕見。有法院就曾指出,“收取的超出銀行貸款利率四倍的利息應逐月沖抵本金。”[118]最高人民法院在近來的判決中也承認了“當期型抵充”的方式,并在裁判文書中列明了詳細的計算過程。[119]
(三)法性質的判斷
[76]對于超額利息的抵充,有法院認為其是“確定本金數額”的作業。例如,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年發布的《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21條規定:“……折算后的實際利率超出四倍利率,超出部分的利息應當從本金中扣減”。該條是關于借款合同本金如何確定的條款。由此可見,這樣的思路是將超額利息的抵充當作“合同解釋”的問題來看待。[120]
也有法院將超額利息的抵充概況視為清償抵充的。例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年發布的《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會議紀要》規定,“借款人尚未按約償還借款本息,在審理過程中請求將已經支付的超過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四倍的部分沖抵本息的,應予支持。”該規定認為超額利息“沖抵”的對象是本息,實際上是基于“清算”的立場做出的判斷。
[77]而學說上,有學者在概況承認超額利息抵充本金的可能的同時,認為超額利息抵充本金實現了債務人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與債權人的債權的“抵銷”。[121]
近來的觀點則區分了超額利息的抵充對象。[122]在抵充同一借款本金的場合,“抵充”的法性質可以解釋為“清償”,也可以解釋為“抵銷”;只要考慮到“抵銷適狀”,兩者在實際效果上并無差異。而若以同一當事人之間的第一借款合同產生的超額利息“抵充”第二借款合同的本金,則此時的“抵充”是以超額利息返還請求權來“抵銷”第二借款合同的本金返還請求權。若超額利息的抵充對象是同一當事人之間“將來”借款的本金,則可以借鑒日本法的立場,[123]僅在當事人存在“抵充合意”的場合才承認抵充的可能。至于“抵充合意”的法性質,則應視為當事人之間的“抵銷合同”。[124]
七、證明責任
[78]借款合同中的貸款人請求借款人歸還本息的場合,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貸款人應就借款事實以及當事人之間的利率約定作出證明。由于《民法典》將借款的實際提供作為“自然人借款合同”的成立要件,“借款事實”的證明更多地與第579條有關。因此,以下的討論將主要關注“利息”及“利率”的證明。另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場,“利息有無及明確與否”屬于事實認定的問題。[125]
(一)貸款人的舉證
[79]對于借款合同中是否存在關于利息的約定,法院的裁判主要貫徹的是“書證優越主義”的立場——書面的“借款合同”是最為重要的證據,“持有借條主張權利”是原告勝訴的開端。[126]只要能表明當事人之間的真實意思,“借據”“借條”“欠條”“借款協議”“收據”“還款協議”“承諾書”等不同名稱的書證都會成為法院裁判的主要依據。[127]貸款人只要能證明借款合同中存在關于利息的明確約定,其關于“借款存在利息約定”的舉證即告完成。[128]但若缺乏“借據、收據、欠條等債權憑證”,則借款有償乃至借款成立的主張都得不到法院的支持。[129]
[80]書面的合同之外,貸款人還可以通過其他證據來證明利息的存在。如借貸雙方均為自然人,在貸款人主張存在口頭利息約定而借款人否認的場合,若貸款人能夠提供借款人簽字的“計息憑證”,也能證明當事人之間存在關于利息的口頭約定。[130]若書面借據在利息約定方面存在瑕疵,只要貸款人能證明借款人存在按期、定額支付利息的行為,借款有償的證明也能成立。[131]此時,借據上載明的金額、歸還時間與事實還款情況的對應以及當事人之間的“談話錄音”對法官“自由心證”的形成有著重要的作用。[132]
[81]另外,若作為原告的貸款人能證明借據金額大于實際借款金額,法院也可能因此將差額部分視為當事人關于利息的默示約定。[133]但這樣的情形并非必然,貸款人如果僅舉證其部分提供了借據載明的金額,法院仍可能會要求其進一步證明利息約定的存在,否則將對此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134]
[82]至于證明的程度,若已達到“民事訴訟高度蓋然性之證明標準”,法院通常就認定借款事實及利息約定的存在。[135]
(二)借款人的抗辯
1、沒有約定利息
[83]由于“沒有約定利息”是消極事實,難以直接認定。因此對于貸款人支付利息的請求,借款人可以單純以“沒有約定利息”為抗辯。此時,貸款人將承擔證明存在利息約定的責任。此時,若貸款人僅主張存在口頭的利息約定而無其他證據證明,則借款人的抗辯成立。[136]
[84]在缺乏約定的場合,對于借款提供時即扣除利息、貸款人以此主張利率及利息的情形,借款人可以根據《合同法》第200條(《民法典》第670條)提出“縮減本金”以及“沒有約定利息”的抗辯。[137]
[85]在借貸雙方均非自然人或僅有一方為自然人時,由于《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限縮立場,借款人除非能夠提供無利息約定的證據,否則將承擔償還利息的債務。[138]
2、利率過高
[86]在利息約定被法院認定或者當事人自認的場合,借款人可以提出“利率過高”的抗辯。此時,借款人通常只要對利息與本金的數量關系作出說明(是否超過年利率上限),即可完成針對“利率過高”的證明;法院也會積極對此作出計算。[139]
[87]實務中也有貸款人因借款合同約定的利率超限而自愿降低利率的情形,在合同的其他內容及相關事實清楚的前提下,法院會支持貸款人的請求。[140]
注釋:
[1] 參見奧田昌道編集:《新版注釈民法(10)Ⅰ——債権(1)債権の目的?効力(1)》,有斐閣2003年版,第342頁(山下末人、安井宏執筆)。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文書中指出:“按月給付利息是民間借貸中常見的情形”;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終234號民事裁定書。另外,本文所引用的判決文書以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例為首選。但由于大多數有關借款合同的訴訟案件是由下級法院審理的,因此在必要的場合,本文也選取了部分下級法院的裁判例。
[2]對于非金融機構的借款活動,尤其是非金融機構的法人出借款項的行為,法院長期認定為無效。但2015年《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發布之后,貸款人是否持有包含貸款業務內容的金融牌照原則上并不影響借款合同的效力。
[3]參見王利明:《中國民法典的體系》,《現代法學》2001年第4期,第46-47頁;張力、龐偉偉:《“民商相對分立”模式下流擔保條款效力規則之重構》,《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第49頁。
[4]如201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一條。
[5]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法發〔2019〕26號)等。
[6]近來的觀點認為,市場上的借款行為有多種類型,利率約定作為締結借款合同的重要動因,在不同類型的借款行為中有著不同的作用,應基于借款的類型作出對應的調整,而非僅僅依賴利率的絕對數額做出判斷。參見劉勇:《利率規制:從“法定”到“市場”》,《內蒙古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第105-106頁。
[7]參見黃茂榮:《法學方法和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頁。
[8]參見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三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272頁。
[9]參見劉勇:《超額利息返還的解釋論構成》,《法學》2019年第4期,第173頁。
[10]不僅是《民法典》,其他法律中的“國家有關……的規定”也可能主要指向行政機構的規定。例如,《招標投標法》第9條規定“招標項目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需要履行項目審批手續的”,其中的“國家有關規定”目前主要就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8年第16號令。
[11]參見《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附件四之三。
[12]參見“中銀消費金融有限公司訴高春明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公報》2016年第6期,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1-54頁。
[13]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終408號民事判決書。
[14]參見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最高法立案庭負責人就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轄司法解釋答記者問》,最高人民法院網站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11361.html(訪問時間:2020年8月30日)
[15]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1990號民事判決書。
[16]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412號民事裁定書。
[17]參見中國農業銀行網http://www.abchina.com/cn/CreditCard/xykts/201812/t20181227_1805701.htm(訪問時間:2020年8月30日)。
[18]參見中國建設銀行網站,http://creditcard.ccb.com/cn/creditcard/service/card_shoufei.html(訪問時間:2020年8月30日)。
[19]相關規定可參見《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關于將委托貸款信息全面納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的通知》(銀辦發〔2014〕153號)。
[20]參見胡東海:《<合同法>第402 條(隱名代理)評注》,《法學家》2019年第6期,第187頁,段碼54。
[21]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1465號民事判決書。
[22]較為具體的說明,參見王林清:《民間借貸利率的法律規制:比較與借鑒》,《比較法研究》2015年第4期,第191-192頁。
[23]較為詳細的說明,參見何小勇:《民間借貸的衍變與法律規制得失探討》,《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第49-52頁。
[2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9)最高法民再195號。下級法院的立場可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網站于2019年11月12日發布的《關于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打擊與防范網絡“套路貸”虛假訴訟工作指南》及相關的解讀(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網站:http://www.jsfy.gov.cn/art/2019/11/12/11_98908.html;http://www.jsfy.gov.cn/art/2019/11/12/11_98910.html。訪問時間:2019年11月26日。)。
[25]參見李想、葛曉陽:《最高法詳解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亮點》,《法制日報》2015年8月10日第5版。
[26]杜萬華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理解與使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515頁。
[27]參見來棲三郎:《契約法》,有斐閣1974年版,第27-28頁。
[28]參見注①,第341頁。
[29]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終271號民事判決書。
[30]參見王利明:《合同法分則研究》(上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頁。
[31]參見注8,第279頁。
[32]參見高圣平、申晨:《民間借貸中利率上限規定的司法適用》,《政治與法律》2013年第12期,第27頁。
[33]遼寧省燈塔市人民法院(2020)遼1081民初1919號民事判決書。
[34]湖北省石首市人民法院(2020)鄂1081民初941號民事判決書。
[35]湖北省黃石市下陸區人民法院(2020)鄂0204民初17號民事判決書。
[36]學說上認為,即使是使用本金的對價,如果并非是依據利率計算的,并不構成利息。參見注1,第341-342頁。但我國的法釋〔2020〕6號將利率規制適用于未必依據利率計算的部分(違約金或者其他費用等(法釋〔2020〕6號第30條),意圖以此來限制出借人的過高收益。實際上,或許完全可以通過“合意瑕疵”來解決相關問題,將不同屬性的金錢統一納入“利息”范疇的話,可能會掩蓋真實的問題。
[37]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190號民事判決書。
[38]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終927號民事判決書。
[39]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1971號民事判決書。
[40]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1880號民事判決書。
[41]如杭州互聯網法院(2019)浙0192民初10032號民事判決書。
[42]參見張宇哲、胡越:《民間借貸利率“紅線”之辯》,《財新周刊》2020年第36期,第38-39頁。
[43]參見李祝用:姚兆中《再論交強險的制度定位——立法的缺陷、行政法規與司法解釋的矛盾及其解決》,《保險研究》2014年第4期,第31頁;劉銳:《交強險基本模式問題探析——從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和國務院行政法規的對抗談起》,《保險研究》2013年第11期,第79頁。
[44]朱寧寧:《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審議民法典合同編草案時建議明確借款類型和利率上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網站(“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npc/c35774/201812/c529fe36abc8407a98bd38028c0419f0.shtml,訪問時間:2019年8月18日。
[45]參見蘇盼:《司法對金融監管的介入及其權力邊界——以金融貸款利率規范為例》,《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第125頁。
[46]德國法上曾經將固定利率與借款合同的終止權相關聯,卻終究無法適應貨幣市場的變化。參見陳自強:《德國消費借貸之修正與債法之現代化》,《臺大法學論叢》2008年第1期,第281頁。
[47]參見何家弘:《從自然推定到人造推定》,《法學研究》2008年第4期,第123頁。
[48]參見肖建國:《論合同法上的證據規范》,《法學評論》2001年第5期,第87頁。
[49]王雷:《論合同法中證據規范的配置》,《法學家》2016年第3期,第65頁。
[50]參見劉定華、芥民:《借款合同三論》,《中國法學》2000年第6期,第109頁。
[51]參見楊代雄:《意思表示理論中的沉默與擬制》,《比較法研究》2016年第6期,第159頁。
[52]班天可:《論民法上的法律錯誤》,《中外法學》2011年第5期,第1016頁。
[53]例如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頁;崔建遠:《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頁。
[54]參見韓世遠:《合同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09頁。
[55]參見劉勇:《合同補充解釋的理論構造與立法選擇》,《浙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第55-56頁。
[56]代表性的學說認為補充解釋在性質上仍然是合同解釋。參見注53,王利明書,第410-411頁。
[57]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終650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824號民事裁定書。
[58]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404號民事裁定書。
[59]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299號民事裁定書。
[60]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979號民事裁定書。
[61]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657號民事裁定書。
[62]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終字第125號民事判決書。
[63]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898號民事裁定書。
[64]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5000號民事裁定書。
[65]對立的學說為“惡意限定說”。可參見劉勇:《溢繳稅款的返還——<稅收征收管理法>第51條的解釋論》,《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17年秋季號,第182頁。
[66]參見藤原正則:《不當利得法》,信山社2002年版,第139頁。
[67]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終字第138號民事判決書。
[68]參見占善剛、王譯:《民事法律規范中“視為”的正確表達——兼對<民法總則>“視為”表達之初步檢討》,《河北法學》2018年第12期,第66頁。
[69]劉風景:《“視為”的法理與創制》,《中外法學》2010年第2期,第199頁。
[70]張海燕:《“推定”和“視為”之語詞解讀?——以我國現行民事法律規范為樣本》,《法制與社會發展》2012年第3期,第107-112頁。
[71]例如,推定可以是訴訟層面的,也可以是實體法層面的。參見森田宏樹:《契約責任の帰責構造》,有斐閣2002年版,第20-21頁。擬制的相關論述,則可參見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42頁。
[72]這方面較為典型的例子是“強行法規”的認定:法規中的“不得”、“應當”等表達僅僅是初步的證明,最終仍然需要通過規范目的來判斷。參見佐久間毅:《民法の基礎1総則》,有斐閣2005年版,第182頁。
[73]注②,第369頁。
[74]參見注26,第 439頁。
[75]參見出雲孝:《近世自然法論における有償?無償契約概念の形成史 : グロチウスからカントまでにおける消費貸借の位置付けを中心に》,《朝日法學論集》50號(2018年),第40頁。
[76]參見山本敬三:《民法講義IV-1·契約》,有斐閣2005年版,第366頁。
[77]參見楊立新:《民間借貸關系法律調整新時期的法律適用尺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解讀》,《法律適用》2015 年第11 期,第12頁。
[78]參見注26,第 443頁。
[79]甘肅省武威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武中民終字第560號民事判決書。
[80]參見崔建遠:《合同解釋與法律解釋的交織》,《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年第1期,第73頁。
[81]See Nicole Kornet. Contract interpretation and gap filling: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twerpen-Oxford: Intersentia,2006, p.139.
[82]參見武川幸嗣:《契約目的の意義と機能》,《法學セミナー》2017年第4期,第86頁。
[83]參見注26,第441-442頁。
[84]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390號民事裁定書。
[85]參見注46,第279、291頁。
[86]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釋義》,法律出版社2020年7月版,第480-481頁。
[87]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46號民事判決書。
[88]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119號民事裁定書。
[89]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4453號民事裁定書。
[90]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2216號民事裁定書。
[91]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號)。
[92]較為典型的如2019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建立疑似職業放貸人名錄制度的意見(試行)》。
[93]如《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防范和打擊虛假訴訟的實施意見(試行)》(甬中法〔2019〕37號)。典型的裁判例可參見溫州市中級人民法2018年10月公布的“8起‘套路貸’典型案例”(法寶引證碼CLI.CR.45931595)。法院多會強調對涉及職業放貸人的借款糾紛應“嚴格審查”,但難道還存在“不應嚴格審查”的情形嗎?
[94]安徽省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皖10民終94號民事判決書。
[95]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區人民法院(2017)浙0902民初354 6號民事判決書。
[96]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國家稅務總局浙江省稅務局印發《關于對職業放貸人征收稅費的會議紀要》的通知(浙高法[2019]100號)。
[97]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4659號民事裁定書。
[98]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打擊與防范“套路貸”虛假訴訟工作指南》第17條(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網站2019年10月22日發布。地址:http://www.jsfy.gov.cn/art/2019/10/22/11_98736.html。訪問時間:2019年11月25日)。
[99]參見趙紅旗、陳素娟:《職業放貸人高息放貸被判無效》,《法制日報》2019年11月6日第8版。
[100]就借款合同而言,重視“主體”的規制進路在比較法上較為常見,但主要的模式是將借款人納入“消費者”的范疇,而不是將規制重心置于“貸款人”。
[101]有學者認為,對于第25條所設定的自由裁量空間“應當有所限制”。參見注77,第16頁。
[102]李國光主編:《中國合同法條文釋解》,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頁。
[103]參見魏耀榮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釋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頁。
[104]近來有學者主張應在區分民商事借貸的基礎上,在商事借貸中進一步區分單方商行為和雙方商行為;前者應受到民間借貸利率規制的限制,后者則應尊重當事人的意思。參見王建文:《論我國民間借貸合同法律適用的民商區分》,《現代法學》2020年第1期,第141-142頁。
[105]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16)最高法民終271號民事判決書。有下級法院認為此種情形可直接適用第211條第1款,參見浙江省臨安市人民法院(2009)杭臨商初字第1253號民事判決書。
[106]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終323號民事判決書。
[107]浙江省桐廬縣人民法院(2017)浙0122民初1023號民事判決書。
關于法院立場的嬗變,可參見江必新、何東寧等:《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性案例裁判規則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263頁。
[109]許德風:《公司融資語境下股與債的界分》,《法學研究》2019 年第2期,第97頁。
[110]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終字第00104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二終字第20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8)高民初字第136號民事判決書等。
[111]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經終字第421號民事判決書;舟山市普陀區人民法院(2010)舟普商破字第1號民事裁定書等。
[112]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371號民事裁定書。
[113]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90號民事裁定書。
[114]劉勇:《超額利息的抵充——以“民間借貸”為對象》,《法律科學》2019 年第2 期,第172頁。
[115]如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終字第00104號民事判決書;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鄂民終字第114號民事判決書;甘肅省慶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慶中民初字第55號民事判決書等。
[116]甘肅省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甘01民初860號民事判決書。
[117]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終11237號民事判決書;
[118]甘肅省慶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慶中民初字第62號民事判決書。
[119]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7)最高法民再113號。
[120]對于此類司法文件的解釋,未必就是制定者的原意。即便能證明制定者的意圖并非如此,可能也無法認為“第三人”的解讀就是錯誤的。法解釋本來就是如此的,“歷史上的立法者”終究是“歷史上”的。
[121]參見黃文煌:“清償抵充探微”,《中外法學》2015年第4期,第1002頁。
[122]詳細的論述可參見注114,第173-175頁。
[123]最判平成20·1·18(民集62卷1號頁28);最判平成23·7·14。
[124]參見森田修:《“過払金充當合意”と“契約のエコノミー”》,金融財政事情研究會:《田原睦夫古稀?最高裁判事退官記念:現代民事法の実務と理論(上)》,金融財政事情研究會2013年版,第443頁。
[125]參見注26,第446-447頁。
[126]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244號民事判決書。
[127]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終466號民事判決書;湖北省武漢市青山區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2070號民事判決書。
[128]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終98號民事判決書。
[129]湖北省武漢市青山區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2070號民事判決書。
[130]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終字第109號民事判決書。
[131]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豫01民終6317號民事判決書。
[132]吉林省樺甸市人民法院(2018)吉0282民初1242號民事判決書。
[133]江西省吉安縣人民法院(2017)贛0821民初2180號民事判決書。
[134]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終769號民事判決書。
[135]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9)滬01民終9730號民事判決書;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吉01民終1115號民事判決書。
[136]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法院(2018)吉0781民初1631號民事判決書。
[137]湖北省武漢市青山區人民法院(2018)鄂0107民初1099號民事判決書。
[138]參見注26,第447頁。
[139]湖南省平江縣人民法院(2018)湘0626民初180號民事判決書。
[140]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19)寧民終314號民事判決書。
主要參考文獻:
1.杜萬華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理解與使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
2.奧田昌道編集:《新版注釈民法(10)Ⅰ——債権(1)債権の目的・効力(1)》,有斐閣2003年版。
